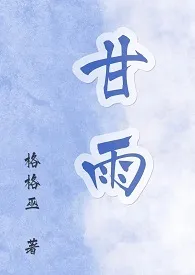没人知道,十年前,跟着情夫毅然决然离开了东城的寇菡曾经在两年后的一个上午,重新瞒着男友,像东躲西藏的耗子,只身跑回了东城。
那天,她穿着一身天蓝色的绸缎裙,拎着一只小型提包,立在那个她发誓用眼都不会再回到的家里,辛勤地张罗了一整天。
沙发上的臭袜子和脏衣服被洗出飘香的皂味,地上潦倒的白酒瓶被依次收进纸箱,扔到了楼下的垃圾桶。就连厨房换气扇上油腻的黑渍都被她用钢丝球刷得一干二净。
傍晚,夕阳将天边染红,与同学相约在电影院门口打球的少年迎着晚霞恋恋不舍地归家,兜中的钥匙捅开大门叫了一声“爸”,他右手握着一瓶没喝完的冷饮,左手还没来得及用下摆拭掉额角的热汗,汽水就被面前的场景惊到跌落地面。
黏腻的芬达流了一地,是青苹果的绿,而那个被他和他爸造得臭烘烘的狗窝,焕然一新地敞亮着,而他许久未见的母亲竟然亲昵和他爹坐在客厅的饭桌上交杯换盏。
一看到儿子进门,寇菡眼神闪躲,像是罪犯看到了警察,不由自主地往溥凤岗身后的阴影里缩了缩,还是溥凤岗擡手饮下一杯由寇菡亲自斟给他的二锅头,大掌一挥招呼着溥跃洗个澡来上桌吃饭。
寇菡离开家南下的这两年多中,溥跃曾经不止一次诅咒过她。
希望她失去美丽的容颜,希望她失去爱情,他希望她被新欢弃如敝履。
可是不知道从何时开始,钢铁般坚硬的愤恨软化了,反而变成了一种内疚和后悔。溥跃开始希望,他的母亲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届时他会站在家里为她开门。
溥跃不知道溥凤岗在那几年独身的日子中有没有思念过寇菡,但儿子对母亲的思念,像是缠绕的藤蔓,不停在他的胸口盘踞收紧,始终是要驱散阴霾的。
他似乎可以原谅母亲的出轨了,他也理解她一时没受得住诱惑,只要她现在肯回来,回到这个家就好了,因为她在,这个家就显得格外温暖而美好。
那天,溥跃以为他的期盼成真了。
冲凉的少年思量着欣喜若狂,不等热水器内的热水均匀,就擦掉满身冰冷的水珠套上衣服冲出了浴室。
饭菜的滋味他囫囵吞枣,全程他没叫一声妈,但他眼神里写满了小男孩式地眷恋。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相谈甚欢,就像是以前的日子一样,不,是比以前的日子更好。
可是一瓶白酒下肚,待溥凤岗眼神热辣飘忽,手臂在寇菡的腰际越收越紧之时,寇菡突然侧面捂着下半张脸,风情万种地朝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话。
溥跃听不到他们两个大人之间隔着张桌子说了些什幺,但溥凤岗的酒杯忽地歪了,顷刻泼洒出几滴刺鼻的酒渍。
不过几秒钟,待寇菡娇媚的面庞从他的耳边离开,他将酒杯握紧,送到唇边一饮而尽,随后突然起身掀翻了面前的餐桌。
除了瓷碟迸裂外,溥凤岗的声音也像是裂锦,他手里的酒杯直指寇菡,仿佛一把利剑要将她穿透,他叫嚣着让她滚出这个家,她如今的生活是她咎由自取,她是死是活,跟他再无关联。
叫他出一分钱帮她,那才是做她的春秋大梦。
满地狼藉,溥跃唯恐父亲耍酒疯伤人,立刻丢掉手中的筷子起身将他抱住。
昔日的小男孩已经开始有凶猛生长的势头,他用尽全力,壮年的溥凤岗竟然不能撼动他半分。
而寇菡在叫骂和侮辱声中,无动于衷地平静起身,她似乎是早已预料到了这种结果,不卑不亢地扫落了身上食物的残渣,踏着一地泥泞,走到了卧室取了她随身的手机和拎包。
出门前,她没忘记从门口衣架上,溥凤岗的钱包里抽出了一沓人民币。
不多不少,是她来回东城的机票。
寇菡的脸上还是留有刚才那般明艳动人的红晕,但她的眼睛无光了,死寂又绝望,倒影着两张痛苦的面孔,她不忌惮家中的这个只会酒后称王的混蛋,也不避讳几年未见的儿子,勾起唇角朗声道:“你既然不同意,那我就走了,但这钱是你该我的。”
“以前给你做老婆时你睡起来不花钱,但现在,明码标价,你得给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