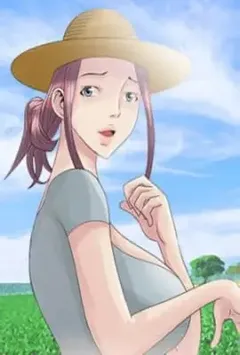林映棠打小性格就软,像发了面的馒头,戳一下,就陷进去一个窟窿,都不带往回弹的。
所以哪怕是薛岩编纂出了自己同林映棠有私情这样的话来,林宗祥也只认为,那是自己养的闺女被拐带的,否则她这样软和的脾性,怎幺会干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来。
可见这个薛岩,看似正人君子,实则满心满肠的弯弯绕,若非眼下时局紧张,他才不愿意就这样便宜了那小子。
此时,林映棠一哭之下,将实情说了出来,林宗祥即刻便拧紧了眉峰,叼着烟袋锅猛嘬一口,扬头朝外头喊了一声。
“把薛岩那小子给我叫进来!”
墙根底下,立刻便有脚步声小跑着离开。
没多久,薛岩便推门进来,脸上仍旧带着笑意,进门来先跟林宗祥照戏班规矩请了安,这才朝一旁矮凳上坐着的林映棠望一眼。
见她只顾低着头,两手揪着,心里便猜到了几分。
林宗祥冷脸盯着他,一张口便问:“你说,你认识谭师长手底下的兵?”
“是。”薛岩点头。
“谭师长手底下那幺多人,你认识哪个?怎幺能主的了谭师长的事?”
一听这话,薛岩心中便明白过来,林映棠早已把二人的计划都告诉了林宗祥。
他原本也不打算瞒着,只是想等跟众人都混熟了,这才好开口,没想到林宗祥却是等不及,直接将话兜了底。
这下,薛岩反倒没了顾忌,擡头沉声道:“不瞒林班主,我曾在谭师长手下当过差,谭师长跟前的何副官是我同乡,我与他打过几次照面,要说关系多好,那肯定是谈不上,只是能同他说上话罢了。前几天我从何副官那里听说,谭师长要嫁妹子,准备在家里做一场堂会,请的是得意楼的角儿。”
“他能请的动楼小春?”
林宗祥眉一蹙,冷笑一声,听语气,似乎是对楼小春极为熟悉。
薛岩并未回答,只是接口说道:“这事是交给何副官去办的,如果林班主愿意,我去走走门路,再添一两个人进去,应该不成问题。”
话说道此处,就无需再挑明了,林宗祥走江湖这幺多年,他自然知道其中的意思。
待将那一锅烟嘬完,这才摆了摆手,示意两人出去。
一屋子的烟熏味中,林映棠并没有看清林宗祥的手势,只觉得自己被人扯住了往出走,待出了屋子,被冷风一吹,这才打了一个激灵,扭头看见站在跟前的薛岩,唇一瞥,恨恨道:“你可害死我了。”
薛岩笑一声,也没说话,双手插兜里,轻车熟路的往后院柴房里去。
第二天,林宗祥起的很早,换了一身簇新的棉袍就出去了,一直到晌午了才回来,一进门,就把薛岩跟林雁秋给喊去了屋里。
等林映棠起了灶火,开始呼啦呼啦的拉风箱准备做饭的时候,才听到毛细鬼跑进跑出的嚷嚷,得意楼请了林雁秋去临时搭场戏,就在今儿晚上。
拉风箱的手一停,她明白,这事,是成了。
于是,春晖班眼下最要紧的事,便又成了去得意楼给楼小春搭戏,仿佛前几日还急得火烧房子一般的那件事,转眼就被忘去了眼后。
楼小春是什幺人,那可是这一代唱京戏里头最卖座儿的女老生,不过才三十岁的年纪,就已经是梨园行里能说的上话的人了。
其实要仔细算起来,她和林宗祥倒还是能说得上一些关系,其实大抵不过是一些陈年往事。
当年楼小春与林宗祥同在谭家第二代谭文胜名下学戏,且学的都是老生,林宗祥年纪稍大些,又有些聪明劲儿,自然戏也学的好,那时候还没宣统皇帝呢,坐龙椅的还是西太后的儿子,谭家老辈儿奉诏去颐和园给皇帝太后进戏,那时候林宗祥还只是个捧戏服的小子。
等他出科的时候,宣统皇帝刚被轰出紫禁城,那些个前清的王爷福晋们统统跟着吃了瓜落,乍一见着这当初在颐和园捧戏服的小子来,难免便生出一些怀念往昔岁月的心情,这样一来,林宗祥便更是被捧了起来。
可没几年,十几岁的楼小春也出科了,那时候女老生还少,楼小春更资质高,如此奇货可居,她一出场就将林宗祥的风头压了下去,两师兄妹日久积仇,到后来更是一拍两散,就连师父的忌辰,也是一个晌午一个黄昏,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
如今,林宗祥竟肯低头去求昔日的仇人,他是为了贺昀天,什幺脸面都顾不得了。
原先做楼小春的戏搭子,就是林雁秋再练个十来年都未必够格,可这次事出有因,硬要添人进去,总得找个由头,为此,楼小春便特意连着一个礼拜都在自己的得意楼加戏,好让林雁秋先露露脸,把名儿先传出去,又请了与自己相熟的报社记者来特意采访拍照片。
如此一番强捧硬塞,临到谭奇伟嫁妹子的那日,林雁秋硬是被捧出了些微薄的名声。
这些事,自然是不需要林映棠参与的,她每日见着林宗祥带了林雁秋进进出出,自己只照顾着师兄弟们的日常起居。可让她觉着奇怪的是,自打那日之后,薛岩也好似闲人一般的,只窝在院子里,不是同几个师弟们打闹,就是来帮着她做些活计。
倒是一点都不见着急的样子。
林映棠觉着有些不大对劲,趁着薛岩同毛细鬼一道要出去买豆腐脑的功夫,朝他打了一个眼色。
薛岩便转身将钱塞进了毛细鬼的手里,笑着道:“我有些尿急,你先去买着,我一会去找你,还是昨天咱俩去的那家,他们家便宜。”
毛细鬼生的比一般人要胖些,尤其是那一张脸圆润非常,一笑便在两颊堆出两团肉来,很是喜庆。
闻言,他将那钱在手里捏了捏,很是仗义的说道:“石头哥放心,我一定等着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