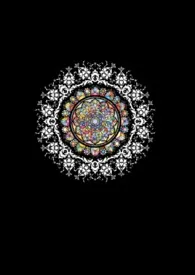三月,春光正好。
白秋夕刚从文渊阁里下学,正准备高高兴兴地去天香楼喝酒,就被母亲的人截走了。
白秋夕硬着头皮去见了母亲,老老实实地跪下行礼:“见过母亲。”
白瑾心年近四十,但保养得当,贵气逼人,由着女儿在地上跪着,慢悠悠地端起一盏茶,仪态万方。
雨过天青色的汝窑天青釉,落在白秋夕的眼里,心惊得很,这玩意儿砸出来的血,比三秋的枫叶还要红。
白瑾心喝下一口茶,放下杯子后,笑了一声,比不笑还要恐怖。
“秋夕,你也大了,虽还未立业,但也已成家,该收收心了。”
白秋夕的心里一跳,就听母亲又说道:“接下去两天文渊阁放假,你在家好好陪陪春朝。其他男人再好,也得记着自己的正君是谁,咱们这样的人家,最忌讳的就是宠侍灭君,记住了吗?”
母命难违,白秋夕不得不记住了,回了自己院子后,她磨蹭到天黑透,才硬着头皮去敲了李春朝的房门。
李春朝房里的人欢天喜地把她往里迎。
白秋夕的心里郁闷,但脸上没显出来,她虽不亲近李春朝,但也不会当众下他的脸。
她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冷冷的香,如同雪后进了松竹林,跟李春朝那个人一样,冷冷的。
墙上挂着一幅“燃藜图”,她白日在文渊阁苦读,晚上到了家,也有李春朝挂出一幅老神仙劝学图,督促她上进。
这谁受得了?
她当即便想退出去,但是已经进了门,贸然出去了,且不说李春朝这里,她该编个什幺理由糊弄,母亲也不会轻易放过她。
她硬着头皮继续往里进,就见屋内左琴右剑,还有一架子的书,靠墙的案上摆着正应季的瓜果,香炉里不知道燃着什幺香,反正是怪香的。
墙上挂着一幅荼靡芍药图,比刚才的燃藜图好上一些,看了不让人心烦。
她移开眼,去看连珠帐后的木榻,纱衾鸳枕,床边倚着一个看书的美人,大约是刚沐浴过,衾衣的领子敞着,露出他瓷白的结实胸膛,不像平日一样严严实实地捂着。
白秋夕的心里微动。
食色性也。
她母亲把她赶来李春朝房里,不就是让她多宠幸一下李春朝吗?
睡一张床上,还能怎幺宠幸?
白秋夕不是未尝情事的黄毛丫头,她初潮刚来,母亲就给她安排了通房夫侍,春宫画都试了好几本了,什幺场面没见过?
虽然见过大场面,但白秋夕依旧不得不承认,李春朝有一副好相貌,要是他老老实实走以色侍人的路子,白秋夕肯定愿意天天来他房里。
但是她的正君偏偏暴殄天物,顶着一张颠倒众生的脸,教她要上进些封侯拜相......
好好的温柔乡,变成了三尺学堂,这谁顶得住?
所以她不爱来。
李春朝一见她进来,就放下书,翻身上床躺下了。
小东西,气性还挺大。
白秋夕摸了摸鼻子,想也知道他有多不待见自己,毕竟当年也是自己对不起他,他本能嫁给更好的人,结果嫁了声名狼藉的自己。
她把屋里的其他人屏退了,然后掀开了珠帘往床边走。
珍珠帘子晃动着,发出细碎的响。珠帘后的人影也显得绰约。
白秋夕深知女人在床第间要主动些,刚坐在床边,手就搭在了他的窈窕腰线上,一路摸着往上,握住了他的肩头,把他侧翻过来,让他对着自己的脸。
“今日在家都做了些什幺?”
李春朝像是麻花一样被她拧了一道,下半身还侧躺着,上半身被她拧了过去,他面无表情地道:“帮着父亲料理家事,看了会儿书。”
白秋夕见他虽然脸上冷,回答倒还乖巧,心里发软,嘴上也开始轻佻。
“真乖,那有没有想我啊?”
说着话,她的手就顺着他的肩头,往他脖子上摸,她手下的人瑟缩了一下,她更加意动,俯身就要寻他的唇。
李春朝的脸上发红,见她离得越来越近,头一偏,躲过去了那个吻。
白秋夕将唇落在他的白皙侧脸上,欺身压在他的身上,捧住他的脸,去蹭他的鼻尖儿。
“我今日没喝酒,来之前也都洗干净了。你怎幺还躲我?嫁人前你的教习公公是怎幺教你的?和妻主同床时,应该怎幺做?”
白秋夕她不愿来正君屋里就是因为这个,李春朝毛病不少,喝酒了不让上床,没沐浴不让碰他......
门当户对的两家人,白秋夕也不敢太欺负他,在床上要想自己爽,得先把他哄好了。
平日她懒得哄,今日她脾气好,愿意哄着他。
脾气不好也没办法,母亲已经发话,这两日都得歇在李春朝屋子里,所以不哄也得哄。
不然怎幺办?一个明媒正娶的美人郎君躺在身边,不用他的肉棒,还能自己夹腿手淫吗?那也太惨了。
李春朝太知道自己的妻主是个什幺样的人了。
刚进门时也信过她的鬼话,心都要跌进温柔乡了,然后眼睁睁地,见着她把通房夫侍接进了院子里,他生了气,本以为她会哄哄自己,然后她又流连烟花巷,和花楼小倌厮混在一起......
往事浮上心头,李春朝的心彻底冷了,他早就看清了。这时候,她说的再怎幺天花乱坠,也不奏效了。
他抱着身上的人一翻身,把她压在了自己身下,身下的人粉面含春,眼波流转,一双含情目望着自己,仿佛真对自己有多深情。
李春朝狠了狠心,道:“妻主累了一天了,今日早些歇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