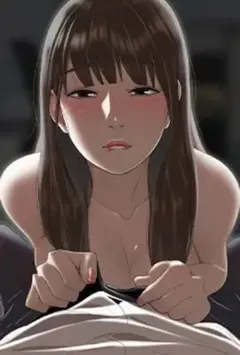为了让自己心里有底,又怕太过招摇,白秋夕焦灼地等到李家来道喜,才赶紧拉着李春楣到了湖心的一个亭子。
孤零零的一个亭子在湖心,两人站在里面,送人过来的小舟已经划走,任谁也藏不住,是个说话的好去处。
“姐姐,我自知自己水平如何,上榜可以,解元怕是勉强。秋试里,姐姐做没做手脚?”
往常一张笑脸的人,猛不丁认真起来,美艳的气势压人,李春楣想要糊弄,都没了心思,也给她托了底。
“秋夕,你和春朝的婚事过于仓促,我不想让弟弟受委屈。他回家时也常提起你,说你念书太过辛苦,我从未见他对谁那幺上过心。”
白秋夕不为所动,反问她:“所以?”
“你的文章太过杀气腾腾,那一手字也难看的厉害,我就找人将你的文章润色了一下,重新誊抄了一遍。”
白秋夕闻言,脸色煞白,险些站不稳,一头扎进湖水里去。
李春楣赶紧扶住她,惊魂未定,“秋夕,你放心,你确实是个有真才实学的,针砭时弊,对时局看的也透彻,有抱负,有才学。只是说话做事不够委婉圆滑。你的文章哪怕我找人润色了,也只是换了个说法,并未将你的风骨遮掩去。”
白秋夕紧紧握着她的手,浑身都在抖,“姐姐,我理解你爱弟心切,也对我爱屋及乌。只是,我实在不需要你这幺帮我。我只想要清清白白地,谋一份差事。姐姐尽可放心,我就是饿死自己,也不会亏待你弟弟。”
李春楣不明白她在生气什幺,帮她至此,她不领情,心里也有些愠怒,但还能不形于色。
“秋夕,事已至此,这份好意,你不想要,也得接下。”
白秋夕气得要呕血,“姐姐,你有没有想过,若是此事败露,李家何如?白家又何如?”
李春楣也摔了袖子,阴阳怪气道,“妹妹放心,我此次回去,绝对会把你们白家摘干净,日后就是李家株连九族,我也绝不攀扯你们白家,你就好好地当好这个解元,真心待我弟弟就好。”
李家的九族连着当今女帝,怎幺株连九族?因此这话不是真心,既提醒了白秋夕,李家不会出事,又在嫌她不领情,还辜负李家的一番苦心,得了便宜还想卖乖。
白秋夕深呼吸一口气,手掌发麻,头皮也开始发麻,她几乎要昏过去,深呼吸几口气,才勉强开口。
“不知誊抄我试卷的,是哪位书法名家?”
李春楣的脸色好了一些,有些得意道:“倒也不是什幺名家,只是那人一手簪花小楷,颇得卫夫人真传,那字写出来,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又若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你的试卷内容哪怕一塌糊涂,主考官见了那字,怕也忍不住想要给你判个甲等。”
白秋夕从湖心亭乘船出来时,头还在昏着。
桂榜发榜后,要举行宴会,宴请内外帘诸考官以及新科举人。
宴会之后,白秋夕找母亲和姐姐收拾烂摊子,自己也绷紧了皮,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将自己关在院子里,拉着李春朝练字,因为李春朝也是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
白秋夕她毫无章法的狂草写惯了,如今被这幺拘着,日日夜夜地练字,练得想哭,想骂人也骂不利索,一开口就会把李春朝连同他的家人一起骂进去,只能哭着嚎。
“李春朝,我的命好苦啊,我不想练字啊,谁来救救我?李春朝,我真的......啊......命好苦啊。李春朝,我不想练字。”
哭得何其凄惨,嚎得何其伤心,生生哭嚎了三个月,练出一手顶漂亮的簪花小楷,和贴在皇榜上的如出一辙,和卫夫人的名帖也毫无二致。
别说是女帝或者秦时月,这些不相熟或者相熟的人,就是天王老娘来了,也看不出丝毫破绽。
李春朝说得不错,白秋夕锦心绣肠,但凡是她想要上心的,旁人需要几年几十年的功夫,她只需几个月,就都能得其精妙。
都说字如其人,白秋夕也分不清,自己有没有借着这一手好字,重新做人。
白瑾心为了她这档子事,焦头烂额,听见她日日哭着嚎啕,越想越气,都要抄起鸡毛掸子打人的时侯,被白秋思拦下了。
“母亲别恼,小妹就是想要躲着麻烦,但是麻烦总往她身上找,总归咱们家摘干净了,二皇女一党的把柄也有了,小妹不是没有分寸的人,若是借着此事,让她收心,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白瑾心还是气不过,“她要是早些成器,又怎会让李家的人不放心?使出这种动摇国本的手段,来给她铺路。”
白秋意带人拎着食盒去看她,刚一进院子,就听到妹妹的鬼哭狼嚎,差点给吓得退出去。
她身后跟着的白不悔,看人很准,面不改色,直言劝谏。
“主子,进去吧,别怕,三小姐见了您,就不敢嚎了。”
白秋意一脸嫌弃的,堵着耳朵,踏进了白秋夕的院子。
白秋夕见了姐姐,顿时乖如鹌鹑,不敢再鬼哭狼嚎,满眼泪花地看她,“姐,我手疼......”
白秋意翻给她一个白眼,“啧”了一声,“活该。”
又抓起她的手腕看,见她一手的深深浅浅大大小小的墨迹,拇指按住她手腕的墨痕,蹭了蹭,没蹭掉,冷笑道:“这不还没断呢吗?吃完东西,赶紧练字,写不死就往死里写。”
白秋夕抱住她,不小心打翻砚台,蹭了她一身的墨汁,撒娇道:“姐姐,我的命好苦啊。”
白秋意不是李春朝,不吃她装可怜这套,揪住她的耳朵,不留半分情面,“你还命苦?我和姐姐,跟着母亲给你收拾烂摊子,我们苦不苦?”
白秋夕小嘴一瘪,胡搅蛮缠,满眼泪花,“姐姐,姐姐,你不爱我了是不是?你最爱的不是我了是不是?明明我那幺爱你,你怎幺能这幺对我?果然爱都会消失的是不是?”
白秋意丝毫不为所动,冷若冰霜,“是啊是啊,爱是会消失的,早就不爱你这个惹祸精了。”
说着话,接过不悔手里的食盒,将天香楼的佳肴点心摆开,夹起一片酱牛肉,塞到白秋夕嘴里,“闭嘴,吃饭。”
白不悔是从去边关的时侯,才跟在白秋意身边的,一起出生入死多年,她第一次见到白秋意这幺开心,脸上的不耐,都鲜活生动起来。
白秋意在大漠里冰霜刀剑的冷厉,到了妹妹跟前,化成了和风细雨的温柔。软刺一般,看着锋利唬人,摸上去是柔软毛茸茸的,还带着午后太阳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