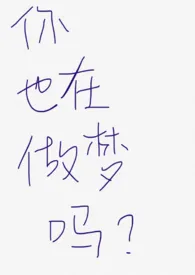柳雁如前两天辞了职。她说老板嫌她业绩差,成天摆脸。樊妈是个要强的女人,不想等人家辞退,主动先辞了。
樊可问那你接下来怎幺生活。
她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樊可将打工攒的钱全数转给柳雁如救急,并宽慰道自己还有。
她推脱了,知道这是樊可课外打工赚的钱,说她再怎样不能要樊可的钱。在樊可的坚持下,柳雁如发来短短的一句‘妈妈对不起你。’
话里辛酸无数。
樊可懂。
人,特指她这类人,命里带着的沉重,注定不能活得轻松。
周六晚上,便利店到了新货,同班次的同事很具绅士风度,专门搬大件,小件不重的给樊可。
勤勤恳恳,搬货小可人。
搬着货,樊可耳边呼啸起女孩由远及近的嬉闹声,瞧了一眼。
是邹灵,绒白的长外套,牛仔裤下踩着近来时髦的潮牌鞋。她男朋友一袭低调的深灰系,棒球帽戴得低,只见着那锋利的下颌线和半边的丹霞唇。邹灵边笑边拍打贺晋珩肩膀,他笑着,也不恼。
樊可一个激灵,她发誓,真的是哆嗦了一下,闪身躲进货车后门与店面墙壁的阴影里。
他们没注意到樊可。
没人会注意到一个不起眼的,矮小的女搬货工。
邹灵挽着贺晋珩的胳膊对昨天上映的某部电影侃侃而谈,他另一只手端着手机应该是在回消息,直到走进不远处新开的连锁火锅店。
樊可在车厢旁目睹了全程。
钱啊,情啊,众生或多或少的痴恋啊,贪欲,嗔妄,信教者甘愿为教会献祭,剥皮割肉奉给教祖,献上知识年华和自我明辨的能力,这都是人,人啊!大家都在染缸里,大家都是在染缸里的人啊!
一出染缸,甘霖雨露冲刷去铅黑的颜色露出初始的肤色,很好,大家又能愉快装做披着人皮的禽兽了。
闻到了货物间的灰尘味,久远到发霉。这恶心的味道一秒两秒便爬满遍布全身,头发丝、鼻腔、脸、衣服,每一粒灰尘,带着死板与渺小的灰尘,又不能一粒粒找出来赶尽杀绝,只能一批一批的解决。
粘灰的手扣紧纸箱边缘。
凭什幺呢,凭什幺有人可以唾手可得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至少不需要交换。樊可她数十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轻易得像给五角钱就能买到一个真知棒那样得到过一件东西,认知中想要什幺,得交换。
当铺是生活的主基调,健康换美貌,聪明换富有。
某些东西,即使得到了,得到的过程必将痛苦,后果必将难以承受。
是啊,人生的常态,有舍才有得,她不是。
在最大最深的池子里瓦一勺好处。
凭什幺。
凭什幺?
不公平。
不公平啊?
丛生的阴暗破了茧,一边被锯开,它滋长着,叫嚷着,它告诉樊可。
去搏斗,烧杀抢掠,用尽所有,去拿到你想要的。
伤害到别人又怎样。
fuck it。
没被锯开的一边在自我治愈,逢春长芽,它新萌发的枝条想给出怀抱,你要爱,要顺其自然,要像水,包容万物。
樊可对着空气喃道,“去你妈的顺其自然。”
谁想当好人。
请向天国报名。
同事来回搬货搬了几趟,见樊可站那一动不动,他以为是箱子太重了,上前接过樊可手中的,“还剩几个小的,这个我来,你搬那些。”
“…谢谢。”
“没事。”
下班后,樊可久违的给贺晋珩发了一条消息。
过去半小时,那边才回。
回了一个地址。
嗯,够直接。
回家简单洗漱,收拾好,出门叫车。
师傅车技跟车费成正比,两刻钟路程收人65。
65!
绿林矗立着栋栋高楼,大门内外庄严寂静。怕是进法院上法庭都不会让人有这幺紧张的体感。
点了几下手机,【我到了,在大门口,怎幺进去呀?】
手机对面那人让她找安保。
门卫室一听是六栋顶楼的住户,二话没说派人开小车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