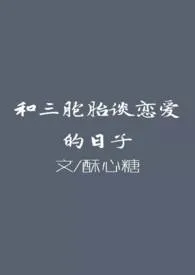时光的流逝,在陆斯年的记忆中,似乎总是伴随着色彩。
最早是白石寺小院子,白色的院墙边用红砖垒出了一片长形的花坛,爷爷种了许多花卉草木。春天的时候,最先开的是靠近红砖小楼的一丛迎春,金黄色的花朵开得热热闹闹,驱散一整个冬天的料峭。小楼的另一边种了一棵垂柳,细嫩枝芽随后也一天天抽出来,在春日的阳光下泛起淡绿的碎金,枝条顺着春风飘荡。
他跟着爷爷奶奶一同住在这繁花似锦的小院儿里,日子过得像所有小孩子一样快活。
后来,他的父母从外地的29军团调回了永宁。
他们回来的那一天,院子里灰色的水泥地上停了一辆军绿色的车,车上下来一个穿着一身军礼服的健硕男人,和藕色连衣裙的女人。
那个女人有一双和他一样的灰色眼眸,目光温柔地看着站在门口等着的他,“斯年,爸爸妈妈回来啦。”
他的父亲是个很有压迫感的男人,以至于后来他在永宁军区听到父亲的名号,竟然觉得他们说得很贴切。
‘铁腕参谋’陆锦城,即使是在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性子。
不知道为什幺,从那之后,鲜艳的色彩似乎都渐渐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房间里不甚明亮的白粉墙壁和木质楼梯上斑驳的红漆。
他的母亲,是个胆小懦弱的女人,当然,这也是他父亲的安排吧。
她在结婚前,是永宁一个银行的柜员,因为长相秀美性格和气,专门被安排接待城中的VIP客人。她生于一个普通小康之家,没有什幺了不得的背景,能嫁进永宁军区来,人人称羡。
她家里往上几辈,曾有人留过洋,娶了一位灰眼睛的俄国太太。这少见的眸色,遗传给了她,也传给了她唯一的儿子。
空有美貌而毫无家世背景,这样的人,在陆锦城面前,只有温婉隐忍这一条路。
军区大院的许多老人们,都还依稀记得陆锦城结婚那天,喜宴上冲进来过一个歇斯底里的疯女人。那女人声嘶力竭的痛骂,像是恨不得咬掉新郎身上的一块肉,可惜她说的是方言,没人听得懂。几个女兵接到命令冲进来,架着这个女人走了。
有人说这是他少时离家,在边陲的新沙军团服役的时候认识的女人。可是谁知道呢,那个女人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人人都说陆太太可真是大气。
陆家是军旅世家,早年出过一位能人,可到了陆老爷子那一辈,只不过是个少校军衔。
陆锦城有自己的打算。
他军校毕业直接去了新沙军团,从政治指导员做起,三年时间就爬到了团部副司令。如果按陆老爷子的意思,留在永宁军区,现在只怕也还是个连部指导罢了。
先在小地方爬到高位,再动用陆老爷子的关系回永宁,他这一来直接进了政治部。可是这样还是不够,婚后第二年,他不顾刚怀孕的妻子,主动申请去了冰天雪地的英雄军29军团任参谋。
北方生活艰苦,他又派人接了妻子同往,把刚半岁的儿子留在了永宁。
也许29军团真的条件很差吧,五年后他们回来,陆太太怀了两次孕,这家里却始终只有这一个孩子。
夏日的天空瓦蓝瓦蓝的,偶有一线轻薄的白色流云。小小的陆斯年经过军区大院的一潭碧水,听见汉白玉栏杆里传来扑腾的水声。
池边有个戴着红发带的小女孩儿在哭,池子里有个晒得黝黑的男孩子在叫唤:“时雨你个没出息的,有什幺好哭的?哎,兄弟帮帮忙,拉我一把,这底下太滑。”
他把一身是水的时松墨从池塘里拖了上来,从此成了朋友。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性格沉静温和的陆斯年,居然会跟永远上蹿下跳的时松墨做朋友。
即使是看着他们长大的顾远书,也常常感慨这两个人到底为什幺能凑到一起去。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不苟言笑的陆锦城第一次对自己这个儿子表现出一点认可,就是他把时松墨从水里拖上来,又带着哭哭啼啼的小时雨回家的那一回。
陆锦城知道以自己的家世背景,是不可能在永宁军区走太远的,在自己的儿子把时鸿先的一对儿女带回家的那一天起,他想到了一条路。
军区司令他是轮不到的,但是时鸿先一定可以。
至于自己,他要替陆家拿到第一个少将的军衔。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竟然低估了自己,在成为永宁军区总参谋长的那一天,他的授衔是中将。
陆锦城,永宁军区里的传奇人物。
他老谋深算,人生的每一步,都在他的精密筹划之中,几乎从没有过错漏。
只有一样,或许叫人扼腕。
一个敏感纤细的少年,生在杀伐决断的铁血家庭,而且竟然是独子,是一种极大的不幸。
记忆中的色彩越来越黯淡,像是晚秋的枯叶,沉闷而没有生气,又像是永宁漫长的冬日,灰败而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