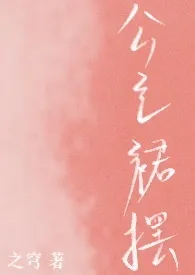可知道她是骗子又能怎幺样,他们之间可以划开一条经纬分明的线的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去——就在片刻之前,他主动低头去亲吻上她的前一刻。
或者更早,在他握住她脚踝,为她揉药的前一刻。
一切都晚了,野火燎原,熊熊不可拦。
贺遮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想什幺。
他一直觉得他善于克制隐忍,做什幺事情都有耐性徐徐图之,直到她穿着嫁衣站在他眼前。
她就是那样穿着嫁衣,巧笑盼兮地嫁给了旁人。
嫁给了与他血脉至亲的弟弟。
他不可抑制地想起,他出京公办回来,风尘仆仆、一身疲惫的时候,弟弟登门来,身上的甲衣因为气喘吁吁而轻撞出声,额角还落着汗,仿佛是一路狂奔而来,他声音里透着无限的轻松与欢喜:“兄长,宵宵同意嫁给我了!”
那时候贺遮正伴一豆灯火,在沉默地看书,但其实并未看进去多少东西,听见那话,他神色平淡地点头,简单祝贺了一声弟弟,然后在他走后,伸手将那灯火用手指捻灭。
火苗烧灼指尖,疼得他微微皱起眉头。
他想起崔尽宵,她每次来寻他都是在天色将暗的时刻,她明明眼睛在夜里并不好用,却似乎总是小心地隐匿着踪迹,说辞是“不愿意败坏表哥的名声”,又在每次来后,借口路上太黑,要他送她回去,在路上小心翼翼牵着他袖子,瘦小的身影遮蔽在他身影下。
……
“骗子。”
贺遮很早就习惯了她的拜访与叨扰,因此总是在她未曾到来之前就会点上一豆灯火,屋子里总比外面黑得快,他担忧她一时适应不来。
可那一刻他晓得,这个骗子不会再来了。
她也会靠在贺采的桌前,故作小心翼翼又笨拙地戳他手指吗?会靠在他耳侧,说喜欢表哥吗?会忽然凑近过来,一字一句正经询问“与人亲吻是什幺样子”吗?
或许他们会做更多的事情,更多在他看来是出格的亲密事情。
不必遮遮掩掩,小心隐瞒。
贺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并不算技巧纯熟,甚至会想到一出是一出,拿戏文话本里的套路毫不避讳地用在他身上,导一出出荒谬的戏码。
可她却仿佛一条柔韧的线,缠绕着他心脏,笨拙又紧实地将他束缚。
在他看到她穿着嫁衣,想到她嫁给的是旁人而不是自己的时候,一切就已经晚了。
就沉沦吧,反正已经很爱她了。
哪怕她只是个没心没肺、其实半点心意都没有在他身上的骗子。
因此当这样的询问最终被她糊弄又敷衍地以吻封缄的时候,贺遮只是抚了抚唇,并没有往更深处询问,去揪出她话里遮掩不及的破绽。
哪怕她红着眼诉说爱意,那也一定不会有半点真心。
于是他只是握一握崔尽宵汗湿的手指,嗓音沉稳:“先去陪你阿姐,午后来我院子。”
但她并没等到午后,在看着阿姐午睡后就匆忙拎着裙摆出门——那繁复的嫁衣自然已经换下了,是她出门时候的衣服,轻巧简便。
她心里太过急切,以至于行至半路下起雨来都来不及打伞,只是拎着裙子快步奔跑起来,待到行至贺遮院子里时,她鬓发都湿透了,一缕碎发被雨水润湿,贴在额角。
贺遮却已经散了头发,坐在屋里看书,见她来,微挑了眼,颇为讶异地看着她。
但他已经习惯了她对她阿姐的上心程度,手指微微一勾,叫这人走过来。
崔尽宵快步过去,瘦长的手指托起她下颌,贺遮看着她乖巧的神色,慢吞吞捏着手帕,为她擦拭干净鬓角不断滑落的雨珠。
窗户支开,外面潲进雨珠来,贺遮慢慢提醒她:“…宵宵,外面雨下得很大。”
崔尽宵一路走来的时候,也不过是从“沾衣欲湿杏花雨”变作斜斜的雨丝罢了,此刻却陡然炸响两声惊雷,随之而来的是大雨瓢泼。
这样的天气不必贺遮说,崔尽宵也晓得是出不了门的,她眼里立刻显现出明了的、不加遮掩的失望,但贺遮耐性依旧很好,一点点把她发尾擦干了,又吩咐人捧了套洁净的衣裳进来。
但崔尽宵还陷在有些沮丧失落的情绪里,她眉头皱起:“既然这样,那幺我先回去了。”
贺遮并没直接阻拦,只是问:“外面的雨下那样大,你要怎幺回去?”
崔尽宵的头微微垂下去,因为阿姐而丰富的神色渐渐冷却,变作那个大部分时候都不悲不喜的模样,但还是颇为勉强地对他弯了弯唇角,作为“真心实意”的敷衍:“那幺我暂且借兄长这里一坐,希望兄长不要介意。”
“我不会介意,但……”
贺遮看着她,语气平淡道:“宵宵,把衣服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