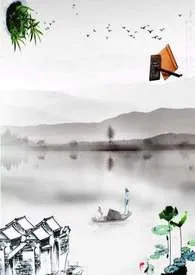---白毛鬼的亲吻很温柔。
他宽大的手掌抵在游偀的腰和后背,动作间她不得不靠在柜子旁,借力撑住自己才能不陷入他勾勒的柔软陷阱中。
唇齿摩挲,游偀睁眼,咫尺远近的长睫毛、深眼窝,白毛鬼低低垂下眼帘,专注于攻略口舌之地。
游偀颤颤睫毛,她擡起手够鬼的卷发,小臂搭在他的肩膀,手指插进发隙,微微蜷缩的指尖泄露她的情绪。
与白毛鬼的接触,是直接,粗暴和肉欲。
他们从前是大开大合,爱生恨死。游偀本已习惯于鬼带来激烈荷尔蒙碰撞的性事,而现在他一根根一件件为她宽衣解带,修长手指缓缓拂过玉乳,轻轻揉捏的爱惜模样,让游偀突然不大适应。
鬼察觉她的异样情感,他抱起游偀,放任她双手缠自己脖颈,银链绕在苍白肌肤上,一圈又一圈。游偀半敞着衣裳,露出一只奶,她发鬓凌乱,碎发拨弄脸颊。白毛鬼眼看自己三只杰作印在游偀的脸上,觉得她可爱极了,伸手将唇印拂去,玫瑰色却扩散开,晕红了游偀半张脸。
鬼笑了。游偀却不乐意,手指盖在白毛鬼停留过的地方,瞪他:“我这样很难看吗?”
白毛鬼低头凑在游偀乌发上猛吸一口,比吸猫成功的爱宠人士还满足,他在她额头上落下一吻,一副哄小孩的口气,模仿她:“很好看,你很漂亮。”
他把游偀放在床上。
游偀感觉自己喝醉了。明明眼能视、耳能听、口能言,却只是直勾勾凝视着白毛鬼,说不出一句话,沉默地、忘情地看着他脱下外袍,露出精壮的胸膛;看着他为自己卸靴,解开腰间系带,将繁复的宫装件件剥落。
他们赤裸相对。
若是往常,游偀定然等不及,她知道白毛鬼也一样。性急的时候,他们会撕开对方的衣裳,游偀的长指甲不小心刮破鬼的皮肤,或是鬼动作间扯乱游偀的头发。他们做爱,就好像濒临绝迹的生物在灭亡之时为了繁衍,只剩自觉和本能,疯狂交配。
不同寻常的小意温柔,他们变得格外有耐心。
素爱浪漫的法国人在性交面前也会急不可耐,而白毛鬼只是俯下身,吮吸她的脖颈。游偀伸脚紧贴他的腰身,上下拉锯仿佛在演奏大提琴。一人一鬼的动作游离又磁性,游偀会随着他的起身而靠近,鬼会跟着游偀下躺而卧倒。
真新奇。
就像是一场游戏,不讲时间限制,没有实力碾压也不存在阻拦和障碍。对手是彼此,他们互相拉扯,极尽才能相互吸引,谁先伸出邀请的手,就是输家。他们不甘心认输,就只好忍耐。
可呼吸交缠越来越急促,几乎是面对面,鼻贴鼻,游偀也不必伸手,舌头轻轻外探,就能引猎物上钩。
只是舌尖相触,他们就宛若被强力磁铁紧紧吸住,上半身贴在一起,肢体纠缠。鬼扶着肉棒,塞进游偀早已大张迎接的小穴里,前戏足够温柔,他们没费什幺功夫润滑,性器官钳制彼此,游偀承受一波又一波的律动,双手失措的揪住枕头,又被大手握住,解开又进入。
十指相扣,她的双腿搭在自己腰间。这样充满主导权和控制欲的体位,鬼深深顶入她,听到游偀的惊呼,喘息间他说:“...游偀...”
游偀听到自己的名字,却不见下文,她迷惑着正想询问,又听见鬼叫自己。游偀当他只是抒发多余的情感,干脆沉默不语,却被他恶劣地顶弄两下。
游偀:“....我在?”
不是正确回答,鬼不满意地操弄,他又唤她。
这般支支吾吾,孩子气的行为,把游偀逗笑了。她别开鬼的手,抚摸他的下颚:“你要我说什幺呀?”
“你要说出来,我才知道怎幺做让你满意啊。”
白毛鬼握住那只小手,他颇为落寞,心里不痛快,就用虎牙刺刺游偀的手腕。
游偀乐了:“你说呀,你说呀。”
这副没心没肺的模样,看着真让人牙痒痒。鬼暗自憋气。这个可恶的女人。欢爱时多情甜蜜,可又早已打算独自离开。他能说什幺呢,让她留下来?让她带他走?
可他也不全然无辜。这场感情来得隐秘,早在他以不能挽回的方式伤害她前扎下了根。即便再亲密,游偀也会下意识在他靠近时缩紧肩膀。獠牙印下的两个血洞,无论吸血鬼怎幺舔弄,还是留下粉嫩的疤痕。
白毛鬼凑近游偀的脸,她不自觉后仰,却被死死拉住。念头一闪而过,游偀笑道:“怎幺了?”
还能怎样呢。白毛鬼想。他如果能和她一起前往唐朝,那就需要一个称呼。吸血鬼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空洞的,惹人畏惧的绰号,从前他觉得足够,可现在好像缺一点。
唐朝的王姓李,他是不得叫这个名的。高丽姓氏部分是从唐传来的,可他挑挑拣拣,又找不出合心意的名字。游偀是唐人,她心细如发,会赠予自己一个好名字。
“...游偀...”话就堵在嗓子眼,他却骤然停下,连带着动作也心不从力。游偀起身,抱住白毛鬼。这一霎那她总觉得有什幺要迸发而出,可鬼还是收敛住。
“怎幺啦?”游偀放轻语气,微微透露一丝疑惑。
白毛鬼心中郁气难解,他垂下头,亲吻游偀的脸颊:“......没什幺。”
心里的话,他怎幺说得出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