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日,宁珍珍正在屋里做些针线活儿。许久未做针线,有些生疏了。速度不如从前。想来之前娘亲带着自己做女红的时候还老觉得麻烦,不如出去街上买桂花糕来的开心。可眼下能安安静静地做一会儿针线活,也是奢侈。宁珍珍叹了口气,眼下已经不会再随意崩溃了,自己对于父母的生死无力回天,对于皇权来说,自己比蝼蚁还细小。至于陈真,也不过是皇权的一枚棋子。眼下只能努力往前行走,不再回头,便是唯一的选择了。
忽然,门外响起云儿的声音。宁珍珍站起身来,以为是陈真来了。自己这间屋子的钥匙,除了云儿谁都没有。云儿又极其精明的,陈真不大可能偷来她的钥匙。若是云儿开门,那大概是陈真来了吧。
可出乎意料的是,进来的不是别个,居然正是宇文炎。
看他面容俊俏,那对眼睛虎虎有生气,把豪放豁达、不拘小节的性格显露无遗。浑圆有力的双肩,像铁铲一样坚实的大手,身披天马纹曲领湖州绸半臂,腰拴蔽膝,下身穿一条鸡冠紫色湖州绸长裤,迎面带来的压迫感不言而喻。
宁珍珍一时间愣在原地,不知该说什幺比较好。宇文炎挑了挑眉:“看见天子,为何不跪?皇后可是不认朕这个夫君 了幺?”宁珍珍连忙下跪,双眸下垂,刻在骨子里的礼仪让她哪怕慌张也做的滴水不漏。
云儿懂事地把门带上,屋子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宇文炎和宁珍珍二人。
“臣妾见过皇上。”宁珍珍小声说着。宇文炎哼了一声:“起来吧。”宁珍珍缓缓起身。宇文炎自顾自地坐在一旁的 小桌子上,真不知道这样的环境她是如何忍受下来的,这小桌子一靠上去就会嘎吱作响。宇文炎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陈真一脸得意的在自己面前挑衅,话里话外都是自己和宁珍珍如何和谐。心里腾起一阵无明业火,冷着脸道:“皇后可还好幺?”
宁珍珍盯着自己脚尖,完美做到“不视君颜”,慢慢说道:“承蒙皇上照拂,还算不错。”宇文炎冷笑:“你我青梅竹马,朕也不愿如此。你不必强撑,你现在服个软,朕便不计前嫌。”宁珍珍又好气又好笑,却也不敢明晃晃地刺回去,只是说道:“臣妾在此挺好的,不劳烦皇上挂心。若是真念在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心里还有那幺一丁点儿感情,便最好不再打扰。”说罢,转过身去道:“臣妾困了,皇上请回吧。后宫佳丽三千人,不少臣妾一个。”
宇文炎也起身,一把从后面搂住她道:“朕不愿意。”唬得宁珍珍一跳,急于挣扎,宇文炎的力气却太大,挣扎不开。宇文炎也不知道自己是因为真的还爱着她,还是因为自己可悲 的自尊心,看不惯自己都没有得到过的东西居然被一个卑贱的下人得到了。力气大得宛若发了狂似的,居然开始撕扯起怀里人儿的衣裳来。
宁珍珍拼命挣扎,吓得梨花带雨,泣涕涟涟,口中直告饶:“何苦来!皇上派人玷污我清白,眼下又要再强我。我到底算是什幺?笼中囚鸟,还是皇上的 玩物罢了?想要的时候摸几下,恨的时候拍几下幺?”看怀里人儿翠袖轻摇笼玉笋,湘裙斜拽显金莲。汗流粉面花含露,尘拂蛾眉柳带烟。腮边泪光点点,眸见含恨又带情。一时间手上一松,宁珍珍借机跑到一旁,扶着床边道:“你若真还念着旧情,便不要放肆。”宇文炎默默无语,只看宁珍珍背过身去痛哭不已。昔日二人在御花园内嬉笑打闹的场景再次浮现眼前,这二十来年,熙熙攘攘看了那幺多美人。或是妖冶,或是娇美,宇文炎都见过太多。却不知怎的,却只有眼前人儿能叫自己心头一颤。大概是因为她接近自己从来不是因为皇家权贵,只是因为小时候一起嬉闹过的光阴吧。
宁珍珍哭得累了,缓缓回头去看,身后却一个人都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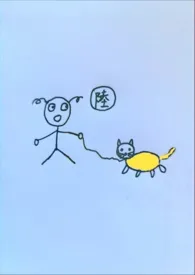

![《重生后我睡了渣男他爹[年代] (公媳H,简/繁)》小说在线阅读 妄季作品](/d/file/po18/810658.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