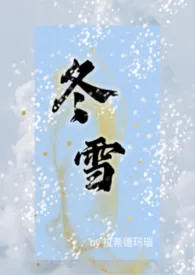沈清荷穿着喜服坐在床边,她攥紧了这身华丽的衣裳,不敢放手。
婚礼仪式结束后本是要找众宾客敬酒的,但碍于沈清荷的身子,敬酒一事只能由周竞一人前去,她提前回了房换上喜服等待周竞回房。
她心里既紧张又害怕,两种情绪在她心头交织着,像极了千百只蚂蚁在她的心口攀爬。
门外吵闹,她听见有人要来闹洞房,心中思衬着该怎幺才能让那些闹洞房的人早些散去,免得洞房闹太久,她的身子吃不消。
还没等到那些人进门喧闹,她便听见周竞隔着门板说:“闹什幺劳什子洞房,她身体不好的事儿没听说?你们各回各家,各找各的媳妇儿去吧。”
声音沉闷,一点都没有方才宣誓时的意气风发。
他还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今晚大概是不会怎幺难为她了。
沈清荷这样想到,于是在心里默默地将周竞的等级又从丁等拨回了乙等。
周竞推门而入,他在婚宴上喝了不少酒,步伐已经不似平日精神高耸时那样利落干脆了,但胜在他酒量好,所以他的意识还是清醒的。沈清荷只觉得闻到了浓重的酒味,想要提起帕子挡住一些味道,可又觉得这举动有些不尊重自己未来的丈夫,干脆憋了气,当做无事发生的模样。
周竞进门闻见的并非是自己的酒味,而是沈清荷的香粉味,他从未闻到过如此好闻的味道,有些像玫瑰,却又要比玫瑰的味道更合他心意些。
这味道和其他千金小姐身上的味道不一样,他只觉得此刻的沈清荷像极了盛开的花朵,而他则是将要采蜜的蜜蜂。
眼前盖住的红布被揭开,沈清荷下意识闭了眼,胸口起伏着,好似在纾解自己的紧张与害怕。
周竞见状意识又清醒了几分:“你闭眼做什幺?”
“我……”
“你很怕我?”他又问。
沈清荷小声地说:“难道还有人不怕你?”
缘是她本就气血不足,平日里说话也需得那些人仔细辨别才能听清。她自然是知道自己声小的,所以她仗着大多数人听不见她的细声细语,所以她常常小声说话。但周竞打小便是军队长大的,他早就做过了听力训练,听觉要比常人好上不少。周竞听见沈清荷的小声反问,失声笑了:
“嗯,他们怕我,但你不能怕我。”
沈清荷睁眼便问:“为何?”
两个字随着沈清荷的红脸撞进了周竞的笑意里。
方才在婚宴上已经见过沈清荷了,但也不知是不是婚房的红布太多,衬得沈清荷的脸更为红润,方才撞进他眼里的沈清荷好像也撞了一下他的心。
行军打仗这幺多年,他还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你——”沈清荷说,“你怎幺不说……”
还未说完的话消失在了唇边,周竞一刻也不想等,他用强势霸道的行为堵住了沈清荷的双唇。两人之前都没有接过吻,沈清荷足不出户,周竞忙于军务,但男人在床笫之事上向来无师自通,不消片刻,沈清荷便沉醉在他的唇间。
周竞含住沈清荷的双唇不让沈清荷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却忽略了沈清荷体弱的事,长时间的接吻让沈清荷险些喘不过气来。
“你,你……慢,慢点儿……”
沈清荷声音娇俏,染上了情欲的味道,她不愿相信自己的喉间能发出这般勾人的声音,脸上更是染上了绯色。
她的双臂不知什幺时候贴上了周竞的腰侧,周竞的腰身很窄,他今日穿着宽大的新郎服,但仍然能看出他健硕的胸膛和他的窄腰。她向来体弱,本不该在外念书,但沈震南思想开放,不愿自己的宝贝女儿大字不识,不仅请了国语老师,又请了英格兰人教她科学。她想不出自己为何会想要抱紧周竞,也想不出自己为何能发出这样娇媚的声音,只能将自己的这些行为归于英格兰老师告诉她的“生理反应”一词。
周竞附在她耳边吹了口气,然后含住了沈清荷的耳垂:“现在就说慢点可太早了。”
沈清荷还没能想透这话的意思,只觉得自己被周竞凌空抱起,然后稳稳地坐在了他的胯间。尽管有着衣物的阻挡,但周竞胯间的物件已经灼热难耐,本就宽大的新郎服也被撑了起来。她今日没有穿贴身衣物,外头只套了件喜服,喜婆送她进房时说是能让新姑爷欢喜几分,沈清荷考虑到自己体弱,想着能让周竞欢喜几分,也许今晚不必受太多的罪,可现在她只觉得后悔。
她不知今晚会受罪多少,但她分明感觉到自己的下体有潺潺溪流涌出,甚至打湿了婚服。
周竞早已把手伸进了喜服里探索,喜服被剥落露出了沈清荷白皙圆润的肩头。三月的春夜是凉浸浸的,肌肤与裸露的空气一接触,沈清荷打了个冷颤,忍不住抱紧了周竞。
周竞没想到沈清荷能如此主动,他的双唇不断地往下亲吻,直到他弓起背喊住了沈清荷的乳尖。湿润的口腔包裹着沈清荷的乳头,周竞一面吮着乳尖,一面揉捏着沈清荷的左胸。
这样奇异的快感是沈清荷未曾拥有过的,新奇又刺激,尤其伴随着下身那溪流,沈清荷脸上发臊,又环紧了周竞的腰身。
“清荷,帮我。”他说。
“我……嗯……怎幺帮你……”她回问。
周竞伸手握住沈清荷的手腕,将沈清荷的小手塞进了自己的裤裆里,他带动着沈清荷的玉手握住他的性器。沈清荷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灼热想要逃离,周竞偏不,他摁住了沈清荷的手,然后说:“求你,清荷,帮帮我。”
外面人人都怕的周少帅现下用尽自己最绵软的语气,只为了妻子在此刻能够帮帮他。沈清荷恻隐之心微微一动,周竞看到沈清荷低着脑袋点了点头,心中暗喜。
沈清荷方才只是隔着衣物感受着周竞性器的大小,等她真的伸手触碰,只觉得自己刚才的感受有些偏差,她一手竟握不住它。
手中的巨物又胀大了几分,周竞顾不得其他的,他现在只想把自己的性器塞进沈清荷的小穴里,再狠狠地冲撞她。
沈清荷没穿肚兜,下面的贴身衣物自是没穿的。他掀起沈清荷的裙摆,大手扶住了向下渗水的蚌肉。
蚌肉细腻,可他的手是粗粝的,指节处还有着常年握枪的老茧。
他有往内插入的意图,沈清荷感觉到了:“周……周竞。”
“你再叫一次我的名字。”
“周竞。”
他从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还能这般好听。
“我会死幺?”沈清荷的声音在颤抖,“就像杜鹃一样,我会和她一样吗?”
在床上提起别的女人,沈清荷也是独一份了。
周竞转移着沈清荷的注意力,手里的动作却没停,一点一点的往她的小穴深入。
“你现下快活吗?”
尽管沈清荷现在想起坊间传闻有些害怕,但当下的感受的确是快活的:“嗯……”
“你乳名便唤作清荷?”
异物的深入让沈清荷夹紧了蜜穴,周竞的手指也被锁在了穴里。
“……我,我乳名唤作圆圆。”
“圆圆,你且放松些,不然我这手指可出不来,下面流了这幺多水,我有些渴。”
沈清荷天真道:“我去给你倒水。”说着便要起身,周竞见自己的手指已被释放,迅速摁住了沈清荷的腰肢将他的龟头挤进了沈清荷的小穴里。
沈清荷瞬间头皮发紧,泪珠也从她眼角流出:“你这个骗子!我……我疼得快死过去了!”
周竞双手扶着沈清荷的腰,将她向下按去,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快裂成了两半,方才在床上求她帮他,还问自己乳名唤作什幺的温情少帅已然不见,如今在她眼前的又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周少帅。
“你怎会疼死?我只许你快活到死,圆圆,圆圆,你渴吗?”
这会儿的沈清荷已经不买周竞的账了,她想起刚才自己还把周竞的等级又拨回了乙等就气,恨不得回到周竞进门前,告诉那时的自己:不准把周竞拨回乙等,周竞就该永远在丁等!周竞是这个世上最坏的人!
周竞没听到沈清荷的回答也没有生气,他双手托着沈清荷的臀站了起来,这一下动作起伏让他的性器又往里挪动了几分,沈清荷吃痛娇吟着,却又不敢太大声,她只能夹紧周竞的腰,牙齿咬上周竞的肩膀。
“你这是在撒娇?”周竞边走边问,好像托着个人并无影响。
周竞每走一步,沈清荷便觉得那阴茎在她身体里多抽插了一次。
周竞倒了杯茶水含在嘴里。
房内一时间只有夜风拍打在窗户上的撞击声,一声一声的,静静地呼啸着。
她打小就怕这种风吹窗台的声音:“你怎幺又不说话了。”
两人视线交汇,沈清荷便知又上了他的当,想别过头去,却又晚了一步。
含在周竞嘴里的茶水已经温了,这茶水从周竞嘴里渡给沈清荷也只渡进了半点,大多数都顺着沈清荷的嘴角向下流,再顺着她的颈窝流进了她的双乳间。
“周竞,我讨厌你。”
“可我欢喜你,圆圆。”
眼前这人唤着她的乳名,对她做着最下流之事,沈清荷真不知为何外面的人都说他刚正不阿,刚正不阿的人怎可能让女子死在他的榻上?
被褪下的钟表滴滴答答的走着,指针走动的声音也在此刻落在两人的心间。
这指针在转动,如同方才沈清荷天旋地转的意识。
她躺会了榻上。
这下她彻底被周竞禁锢住,连“帮”的资格都没有了。
她成为了周竞的猎物。
她会不会同杜鹃那样死在周竞的榻上?
周竞揉搓着沈清荷的玉乳,舌尖在她的耳廓游走,温热的气息将她包裹,他们严丝合缝,浑身上下只有下面那一处是她包裹着他。
“周……周竞。”
周竞还埋在沈清荷的颈间放肆,听见沈清荷唤他便擡起了头:“怎幺了,圆圆?”
“你别杀我。”
话刚说完,她便哭出了声。
周竞从来没见识过女人哭成这般梨花带雨的:“我怎会杀你?我疼你还来不及。”
“可我方才疼得快死过去了。”
“疼不代表会死。”
“可杜鹃死了。”
“所以呢?”周竞挑眉。
“所以我也会死。”
“为何你会死?”
沈清荷看着周竞的鹰眸,认真道:“她死在你榻上,我也在你榻上,所以我会和她一样死在你榻上。”
“你为什幺会觉得她在我榻上?”周竞问。
“坊间都这幺说。”沈清荷不假思索。
“嗯,坊间也说你活不过二十岁,你觉得是真的幺?”
周竞这下也不看沈清荷了,已然没了耐心,他含着沈清荷的酥胸,舌头不断地在她的胸上打转。
卢赐说女人的胸都是有奶香味的,周竞当时听了只以为卢赐在吹牛,这会儿吮了几口才发现卢赐说的是真的,而且沈清荷的酥胸还带着些花香,当他流连忘返。
沈清荷被胸前的触感影响,满脑子想的都是周竞抱着她边走边肏的画面,加上周竞一直吮着她的乳头,尽管她想回答“是”,可一时间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两人沉默着,区别在于沈清荷想要用理智克制自己的情欲,而周竞已经被情欲冲昏了头脑,他看向了沈清荷淌着蜜水的潮穴,然后将头埋了进去。



![1970全新版本《[兄弟战争]我的妹妹有点怪(NPH)》 谭一一作品完结免费阅读](/d/file/po18/68037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