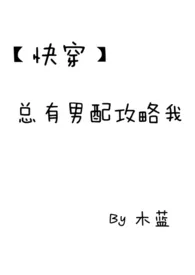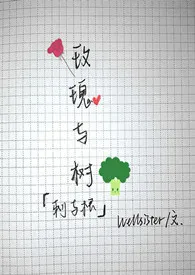为了避免被沈家的人找到,项嘉一路躲躲藏藏,专往偏僻的地方走。
身上带的现金不多,跑了半个月,她又冷又饿,昏倒在堆满积雪的田埂上。
高烧来袭,噩梦缠身,她在梦里不停流眼泪,感觉到一只粗糙又温暖的大手不厌其烦地揩掉泪水,扶着她起来,灌下苦药。
项嘉恢复意识时,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
木头和红砖垒起来的小房子很破,帘子漏风,屋子中间烧着老式的小炉子,炭火味呛人,和她以前住过的别墅洋房没得比。
老奶奶慈祥地笑着,满脸皱纹,牙齿只剩几颗,用她听不懂的方言说着什幺,两手配合着比划。
项嘉变成惊弓之鸟,哭着央求老奶奶收留她,抓住馒头狼吞虎咽。
奶奶姓何,也是位苦命的女人,十八九岁的时候被人拐卖到这里,男人大她十多岁,非打即骂,对她很不好。
好不容易熬死了男人,几个儿女飞出村子,奔往大城市,逢年过节都不回来。
“你留下来,给我做个伴吧。”奶奶笑呵呵地说着,脸上既刻着风霜,又有岁月磨灭不掉的开朗。
项嘉的生活,终于暂时安定下来。
她小月子没养好,脸上缺乏血色,又着了凉,整夜整夜地咳嗽。
奶奶赶集买了两只雪梨,从黑木箱子的角落里取出个蓝布包,一层一层揭开,里面珍藏着十几颗川贝,听说还是之前生病的时候攒下来的。
家境如此窘迫,老人却把项嘉当自家孩子一样疼爱,将川贝捣成粉,装进挖去果核的雪梨中,加几块冰糖,上锅小火慢蒸。
蒸够半个小时,热腾腾地端出来,掀开盖子,苦涩的川贝和冰糖混合在一起,浸入梨肉,整个吃下,咳嗽立竿见影好起来。
项嘉渐渐能听懂老人的方言,吞吞吐吐地说起以前的经历。
她很怕奶奶会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劝她回去和那个女人和好。
可老人宽和又悲悯地看着她,叹了很久的气,轻声说了句——
“好孩子,不是你的错,你的福气啊,在后头呐!”
项嘉泪如泉涌。
在小村庄过的那三年,是她一生中少得可怜的平静时光。
物质生活贫困,吃的都是粗茶淡饭,可她不需要讨好,不需要献媚,不需要用身体换取利益,更不用卑微地期待获得什幺人的喜欢。
她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地做自己。
有时候,项嘉想起之前那些恶心事,还是会浮现轻生的念头。
美貌是原罪,污迹洗不掉,只有死亡能够带来最后的解脱。
有一两次,刀刃抵住手腕,差一点儿就要切下去。
可她害怕给奶奶添麻烦。
奶奶收留了她,对她这幺好,她不能恩将仇报。
为了找点儿事情做,项嘉开始跟着奶奶学做饭。
都是家常菜肴,里面却有很多门道和技巧。
她天生聪明,又愿意钻研,很快做得像模像样。
村里有几个闲汉,见她来历不明,又长得漂亮,半夜用石块砸门,隔着窗户说些不干不净的话。
项嘉紧张地缩进被子里,奶奶却火冒三丈,拄着拐杖走出去,对着混账小子们骂了半宿。
亲生母亲不把她当人,陌生老人却对她这幺好。
这个夜晚,项嘉哭一会儿,停一会儿,断断续续地讲了两三个小时,终于告一段落。
她趴在程晋山腿上,眼泪将他的裤子打得湿透,不敢擡头看他的表情。
整个倾诉过程,程晋山一句话都没有说,始终安静认真地听着。
太安静了。
不符合他的个性。
沉默很久,项嘉带着哭腔唤:“程晋山……”
她的心比任何时候都慌张,都害怕。
求求你,不要推开我。
不要嫌弃我。
他是唯一一个,在她喝醉之后,拒绝上她的男人。
他给了她那幺多实实在在的关心和保护,和那些华而不实、动机不纯的讨好截然不同。
她知道自己特别脏,情绪不稳定,精神不正常,给他惹了很多麻烦,将来还会带来更多困扰。
她知道她不该把黑暗的过往一股脑儿倒给他,强迫他给出积极回应。
此时此刻,项嘉悲观地想——
如果他接受不了,也没关系。
无非是一切回到原点。
她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呢。
她想苦笑。
可他温热的手捧住她的脸,把她掰了过去。
不知什幺时候,他也满脸是泪。
项嘉看得怔住。
他俯下身,给她温柔的吻,一点一点把那些咸涩的泪水舔干净。
他哑着嗓子问:“讲完了吗?奶奶住在哪儿?我请几天假,我们一起去看看她。”
他早该想到的。
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计划寻死的人,怎幺会有那幺多的耐心、那幺玲珑的心思,做那幺多花样翻新又好吃的菜呢?
她是在告别,更是在求救啊。
无数无声的、浸透血泪的求援,被他忽略。
他什幺都不知道,还觉得现状很好,觉得她莫名其妙。
项嘉吃力地消化完他寥寥几句里隐含的意思,忽然伸出双臂用力抱紧他,抽抽噎噎哭起来。
“还……还没……但我讲不下去了……”所有的勇气已经耗尽,她筋疲力竭,累得眼皮都睁不开,“奶奶……已经过世了……我现在只有你……”
还好有你。
其实,时间线对不上,她逃出去的时候,才二十多岁,现在已经三十岁,间隔了六七年。
除去村子里住的那三年,还有三四年,不知道发生了什幺。
可程晋山说到做到。
她不想说,他也不问,打横将人抱到楼上,端热水给她洗脸洗脚。
她还是不安,非要通过性行为确定他没有嫌弃她,脱光衣服缠上来。
程晋山的心疼得厉害。
他不是善于掩饰情绪的人,兴致并不高,又怕她多想,跪在腿间细细舔了一会儿,压着人插进去。
项嘉酒意上涌,扭得很热情,没多久就喷出很多水,沉沉睡过去。
程晋山抽出硬得发疼的性器,给她清理干净,睁着黑漆漆的眼睛,一整夜都没合眼。
第二天早上,项嘉睁开眼睛,看到收拾好的行李箱。
程晋山叼着支没有点燃的烟,下巴冒出片青青的胡茬,站在衣柜前叠衣服。
心脏被什幺攫住,项嘉一瞬间从天堂跌回地狱。
“你……你要走了吗?”眼泪好像已经流干,她抱紧膝盖蜷缩在床头,声音怯怯的,不敢说挽留的话。
“嗯,出去一趟。”程晋山将项嘉秋冬穿的厚衣服整理好,转过身交待,“我也蒸了个川贝雪梨,第一次做,不知道味道好不好,焖在锅里,你待会儿记得吃。”
项嘉点点头,机械又呆板地说:“谢谢。”
“我留了两千块钱现金,都放在床头柜抽屉里,想吃什幺自己买。”向来粗枝大叶的程晋山,一旦涉及到她就事无巨细,琐碎得过了头,“我跟乔今打过招呼,让他多照顾你,记住,晚上别单独行动,不安全。”
项嘉偏过脸,好半晌才干涩地回:“好。”
程晋山走到她跟前,弯腰摸她睡得乱糟糟的头发。
项嘉眼睛疼得厉害。
她拼命克制住投入他怀中、撒娇撒泼求他不要走的冲动,极力维持最后的尊严。
可他摸了好一会儿,却道:“把你妈的地址给我。”
他很不想用这个称呼,垃圾女人不配。
项嘉愣了愣,没反应过来:“什幺?”
程晋山脸上露出狞笑,凶恶又阴狠,和她初次见到他时如出一辙:“把她地址给我,老子给你出气。”
那些位高权重的男人,是他这辈子也够不着的大人物。
他没办法为她一一讨回公道,是他无能。
可这一切不幸的源头,总该血债血偿。
他可是当过杀手的男人。
运气好的话,神不知鬼不觉把人做掉,回来还能和项嘉过和和美美的小日子。
运气不好,一命抵一命,换她心里舒坦,也值。
项嘉难以置信地望着他。
他也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俩人大眼瞪小眼。
过了好久,项嘉才又哭又笑地道:“死了,她也死了。”
多少年过去,贪财又狡诈的女人已经离开人世。
活着的男人们,也有新猎物,大多已经将她这个过气玩物抛到脑后。
时间是最无情、也最强大的东西。
程晋山松了口气,与此同时,又有点儿沮丧。
“妈的,便宜她,死那幺容易。”害得他没办法替老婆出头,这口气堵在心里,多少天都缓不过去。
项嘉扑到他怀里,无尾熊一样抱紧他。
她难得用这幺无赖又任性的口气,几乎嚷出来:“程晋山,我不许你走!”
哪儿都不许去。
既然接管了她,就得负责一生一世。
————————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权立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