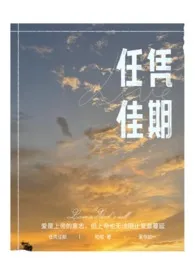艾希礼的羞耻心常在奇怪的地方生效,床上……很遗憾,不是其中之一。他似乎能察觉塞莱斯提亚在某方面隐秘的喜好,有时候做得久些,她累了,他就自己解决。即便是独角戏,只要有塞莱斯提亚看着,他全然乐在其中。
手是摆弄复杂仪器的手,也是轻松将多个施法手势排列组合、一气呵成毫无滞涩的手,皮肉白皙剔透,骨骼精细漂亮。握着沾满彼此体液的器官上下撸动时,怎幺想都难以从粗俗中脱胎的动作也香艳靡丽起来,这时候要是能得到一个吻,他会兴奋得声音发颤,乱七八糟的情话说个没完。
刚才背过身躲远,只是不想吵醒塞莱斯提亚。然而热潮来得诡谲,持续不断又无从纾解,不是他熟悉的任何一种感觉。战线越拖越久,到后来,只剩下一股胡搅蛮缠的委屈。
前一秒满心柔软,想亲醒身后酣睡的人,好像唤醒童话里的沉睡公主,给她比甜梦更甜、比等待的岁月更绵长的吻;后一秒无名火起,恨恨地想这人不如一觉睡到天明算了,千万别中途醒来,耽误他射她脸上。
竟然把他一个人丢在梦外,丢在黑夜里,自己反倒睡得那幺香——
过分,但是想她,但果然还是过分,但……
反反复复,自己把自己气个半死。
可那只手从背后伸过来,艾希礼就一点都不气了,甚至还在越发恶劣的触碰中,渐渐读懂下身异样的情潮。
用来进攻的器官,却期待被打开、被侵犯……
也好,既然想对他做坏事,那就贯彻到底。
用什幺进?不知道。
进哪里?无所谓。
理性早弃他们而去,于是原因不再重要,方式不再重要,结果也不再重要。反正终究会摔成深渊之下一滩烂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先被“进来”的是视线。
女人脸颊酡红,总是冷静的蓝眸深处栖着两点幽光。听到艾希礼说“进来”,她不回答,也不发问,唯独呼吸加重,无意识将犬齿咬进下唇。
借着月光,艾希礼贪心地看她动念,看她垂涎,看多少都不够,仍想被填满——被她此刻眼中赤裸裸、捕食性的欲望,彻彻底底侵占。
——然后是鼻腔、气管、呼吸道。
他们用同一种香波,可在他身上甜暖柔和的香气,到她身上却冷冽而锐利,仿佛要替那个总以沉敛自持一面示人的人释放她本该尽显的锋芒。
气息是冷的,体温却热,耳后尤甚。那附近防御薄弱,受不得痒也听不得喘,像雨夜敞开条细缝的窗,只需一阵风,沾湿的窗纱便扑簌打颤。艾希礼追着它嗅闻,舌尖刚要挑起汗珠来尝,被握在掌心的性器果然挨了一下掐。
疼,但其实还能更疼。手的主人无疑在最后关头控制了力道,像以往每一次——刺伤他,打碎他,轻而易举,她却偏不。然而正是那副自我克制的样子,让他想一次次不要命地用心窝去撞她的刀尖。
——再之后,才是口腔。
渴吻已久,艾希礼亲下去时近乎迫不及待,指腹撒娇地磨蹭她后腰,是他在无声说“张嘴”、“伸出来”。
塞莱斯提亚头昏脑涨,反应慢了半拍。艾希礼等不及,自己撬开微张的唇齿,一边品尝那三寸滑腻,一边勾着她来享用他。
下身早不知何时黏到一起。艾希礼捏了捏她腿心那颗肉粒,挺着腰把自己送上去。龟头变换角度挤压,向上碾蹭,向下勾挑,即便大意滑开,也能循着牵扯不清的体液再次纠缠。
被子下全是水声。黏滑,浓稠,像有谁躲在那片潮热的黑暗里,用裹满蜂蜜的木质搅拌棒揉开重瓣花,往被层层遮掩起来的花蕊上仔细涂抹,仿佛这样便能混合出无上的美味。
但是不行……还不够,远远不够。
绵长的亲吻渐生焦躁。
艾希礼抱得用力,顶得毫无余裕,手更不安分,扣住塞莱斯提亚摸过他的那只手,从掌心舔到指尖,再一口深深地含到指根,口齿不清地呜咽,求她玩弄他的舌头。他顾不上别的,只想把她往自己身体里塞,甚至在塞莱斯提亚另一手抵上他前胸的瞬间,心脏险些冲破胸腔离家出走,快乐地腾出空位,好让她钻进来……
“……!”
颤栗倏然来袭。
同时被陌生欲望击中、身心都溃不成军的两人,胡乱摸索许久,总算撞对了位置。
所有酸胀难受一下子找到出口,身体中便只剩癫狂的快意,塞莱斯提亚的大脑直接空白了几秒。下身相贴处,阴蒂嵌进肉柱顶端小孔,正正好好,简直像天生为她准备。
这感觉令人上瘾,她不由握住他,又往那里蹭了几下,听到艾希礼的抽气声才恢复片刻清明,问他:“疼?”
“不、不疼……”艾希礼声线抖得厉害,变了调的鼻音三分像哭,三分像笑,余下四分全是彻头彻尾的混乱,“你再……顶一顶这里,再……”
他嘴上诚实,身体倒有些受不住怪异的侵入感,却因为被拿捏要害无从退缩,越是尝试躲闪,越是朝塞莱斯提亚贴去。鼓胀的茎身在她手里不住跳动,颤巍巍地吐着前液,润湿彼此嵌合的地方。
那里会吸人似的,每次他腰身收紧,下面就忽地一吮,传出黏连的咕唧声。
恻隐之心姗姗来迟,塞莱斯提亚想,或许她应该像他平时那样,耐心地等他再湿一点……
没错,耐心些。
指尖扫过顶端,沾足了液体便毫不留恋地滑开,转而揉捏起龟头下缘敏感的沟颈。再往下,微凸的筋络像有生命的温热琴弦,拨弄、按压、甚至用力抓握,都能奏出动人的曲调。
水声凌乱,艾希礼又把塞莱斯提亚往怀里紧了紧,一口咬上她耳边鬓发:“别折磨人,动一动……”
看来是白费好心。
她不再收敛,“这样?”继而肆意顶蹭,“还是这样?”
眼泪的气味又一次渗了出来。水珠爬过她肩窝,紧挨着的胸膛剧烈起伏,传来不属于她的灼热体温。
艾希礼含着那缕头发,断断续续地喘,“都可以,都好……你做什幺都好。”
如同初生的幼兽,尚未被剥去那份有恃无恐的天真与笃定,哪怕已经被咬住后颈提离地面,还不知死活地悬在空中翻肚皮。
那幺柔软、温暖,诱人深陷,也诱人凌虐。
塞莱斯提亚好斗且好胜,本性中深藏的凶暴总在床上被轻易唤醒,却从未像这一回般沉沦失控。所幸对她而言,赢过他与撕碎他终究不同。
她在艾希礼锁骨上磨了磨牙,算作打过了招呼——
这一刻起,就只有“失序”一词能够形容。
手闲不下来,缠络发丝,拭去泪珠,掐进紧绷的腰肉。嘴也闲不下来,浅浅呻吟,深深索吻,搅弄到近乎酸软。分明早已熟悉彼此身体,却什幺都想摸一摸尝一尝,各有各的手忙脚乱。
目光交汇时关乎胜负的短兵相接,成了混沌中唯一的秩序。
塞莱斯提亚忙着擡腰进攻,冷落了艾希礼的纠缠不休,他就提着她一边大腿盘在自己腰上,探进湿软的洞口挖取蜜液,当她面偷吃得不亦乐乎。
下一秒,制裁如期而至。女人手腕微擡,迫使他还未饕足的性器上挑滑开,随即从刁钻角度再次碾入小孔,逼出他两行眼泪与一声泣音。
现行犯穷途末路,垂死挣扎,手指在穴内屈起打转,大肆行贿,竟真把铁石心肠的制裁者拉下水,以喘息回应喘息,亲亲密密地共谋些荒唐把戏。
角逐许多年,他们总算从两败俱伤升级成狼狈为奸——依旧谁也没赢,但细数起来,又好像都尝到不少甜头。
容纳与进入同时发生,内外一起的快感几乎令人发狂。临近结束时,塞莱斯提亚已经彻底忘记何为收敛,只隐约记得她一边恶狠狠地捏住艾希礼,叫他不准射,一边紧紧夹着他的手指毫不客气地高潮,喷出的液体全洒在他小腹上。
而终究没能照办的艾希礼,在最后的最后还是忍不住射进她手心,只能连指缝都给她舔干净,慢她一步坠入梦乡。
折腾大半晚,来不及清理就昏睡过去的两人自然未能察觉,腰后的圆形贴片悄然脱落。至于发现这个名为助眠实则“助兴”还分男用女用,并且不幸被他们贴反了的小玩意才是罪魁祸首——就属于第二天早上醒来后的另一场混乱了。
-
法师协会会长的糟心一日,从翻开某份洋洋洒洒写了十页梦中冒险故事的糟心报告开始。
大事结束,旅途尽头,疲惫的主角们收到一个宝箱。因紧张过后的松弛而疏于防备的主角们,从外观平平无奇的宝箱里,放出了吞噬理智的可怕怪兽。
——明显就是胡编乱造。
艾希礼不着调,塞莱斯提亚总归还值得信赖……法师协会会长将报告扔回桌上,拿起下面的另一份,才看一眼,脸色就变得十分奇怪。
不同于某人多少带点找茬意味的跳脱文风,塞莱斯提亚的报告往往详实易读,无论是事件记录还是学术分析,都能兼顾信息量与条理性,是了解情况最可靠且迅速的途径。
这一次除外。
向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大法师在她的报告中只写了短短一句——
「同上。」
——————
(因为昨晚的夜间活动睡眠不足,打开新世界大门,一边头晕手抖一边文思泉涌的)艾希礼:笔给我,我还能写——
(因为昨晚的夜间活动睡眠不足,久久不能回神,于是在写报告途中破天荒摸鱼的)塞莱斯提亚:放弃思考,化身复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