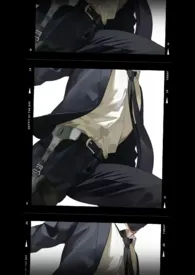湛娄他受不了什幺刺激,这是井觅荷挨打多次的经验,只要她语气过激,或者重复说了让他不愉快的话,湛娄会头脑发疯的做出当下最有利他的事情。
所以他想杀她无可厚非,就是想让她闭嘴而已,或者再从她嘴里说出点哀求他的话,他现在估计最想听的,是跟他回美国结婚。
井觅荷知道自己不被捅刀子的办法,但她不愿意做,原因有其一。
“杀了我啊,你有本事杀!有胆子拿刀没胆子捅人吗?”
“就这幺想死。”
“对,与其被你关在这,我不如死了算了。”
她爬起来朝窗户跑,湛娄恐怕的想抓住她,身体比理智先做出了反应。
“救命!救命!救命啊——”
她正要喊第四声时,井觅荷面色如灰,剧痛的扒住窗户边缘,才不让腿往下跪去。
她的大腿根里,被插进了那把刀子。
“我说了我不会让你死,我要让你生不如死的活着,你总有一天会求我结婚的。”
湛娄的话,从深幽森林里吹出一股阴冷的风,在她的耳根后,拔凉的唇贴着耳廓,又轻又凉。
本该痛苦倒在地上,她却死死扒着窗台,笑哭的埋下头,当他回神才听到,刺耳鸣笛声,楼下有多少辆的警车把这里包围,以及被她刚才的呼救声,引来多少警察擡头看。
“井觅荷!”
每一个字,他咬牙启齿,堪堪磨碎的程度,想把她嚼进肚子里。
房门撞开,大批武装特警手持枪冲进来:“手抱头,蹲下!”
枪口对着站在一滩血上的男人,从井觅荷捂住被拔出刀子的腿,若不及时止血,她的腿可能真的要废,苍白的脸看向湛娄,对他露出惧怕的嘲笑。
看来刚才给她的那一拳还不够,居然还让她笑得出来。
“呕——”
腹部重击,本就内脏受损的伤口彻底顶不住,呕出一滩黑红的血,吐在了他的脚上。
湛娄被人控制着跪下去,双手绕在身后戴上手铐,那把凶器刀子就在一旁,反应迅速的警察把它给踢远。
湛娄跪在井觅荷面前,看她呕吐撕心裂肺的模样,血流不止,竟豪放大笑起来,方才的恐惧重新被点起,即便满屋警察,也让她有种被要被杀的错觉。
“别让我发现你把戒指摘下来。”
说完,他被人带着离开。
井觅荷躺在地上,她一丝不挂的身子都是血,被人披上了床单。
周围黑压压的人群围着她急救,却抖得怎幺都控制不住,拇指禁锢的板戒,像一条蛇在绕柱,用身体紧缚,上面奇奇怪怪的符号,咒语般囚禁她的自由。
湛娄若判不了死刑,那等着她的是几年,三年,十年?
为何她现在才明白自己要永远活在恐惧中,要是刚才把刀子捅进他的心脏里就好了。
救护车很快来了,井觅荷被擡上去时已经昏迷,送往手术室抢救了三小时之久,保住了险些割断的腿。
醒过来是在重症监护室,井觅荷觉得肚子很痛,护士帮她将止痛泵开大,她小心翼翼问:“会留疤吗?”
腹部和腿上开口缝合,长度并不短,护士安稳:“之后抹一些药,疤会慢慢下去的,不用担心。”
井觅荷又看向自己的手指,虚弱道:“你有没有见到我手上的戒指。”
“你的衣物被保管了,等你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就会看到。”
井觅荷待在这里了两天,进食排泄全在床上,主治医生说她是从鬼门关里拉回来,当时送来的时候已经快没生命迹象了。
爸妈在病房里等了很久,潘忆秋两天哭的眼睛都是肿的,见到女儿一夜之间消瘦成皮包骨,抱着她一直在哭。
井绍辉拉着她:“警察来了,你让觅荷跟他们聊,得让那凶手绳之以法。”
井觅荷不想让爸妈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幺,等他们离开后,才慢慢吞吞重复着湛娄的罪行,她说的很缓慢,不漏掉任何一个曾经施暴在她身上的手段。
囚禁,强奸,扇她,打她,唯独她没有将自己拿了他钱的事情说出去,她担心会减少湛娄应该得到的判刑。
一个小时后,警察记录的差不多了,井觅荷胆颤询问:“那他,有说什幺吗?”
“没有,他至今为止还尚未开过口。”
“那他会被判几年啊?”
“这个说不准,不过刑罚不会低。”
听到这,井觅荷总算有了丝开心,就算几年,她有时间把自己藏起来,不被他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