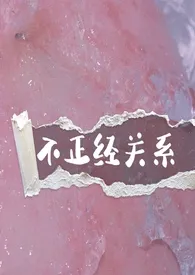狼崖寨的寨主前些日子死了。
福州官衙外面挂了六七年的那张六千两白银的通缉令也终于被撤了下来。
寨主一死,狼崖寨的山匪门散了大半,剩下的人跟了曾经的二当家,做些劫掠商路,烧杀村伙的勾当。
若说曾经狼崖寨是名声在外,现在也只是剩下街坊间的几句闲言碎语,说的也都是恶事。
没了福州百姓的袒护,剩下的几十匪众很快被官府剿了个干净,为首的二当家有些武艺,本来都说要带着弟兄们招安了——官府可不干。
几年来多少官银被他们劫去?
就是寨主死了,剩下的人也得跟着陪葬。
不然总有人抢了官银去,在民间散财,不过两年,就没人愿意来福州做知府了。
大暑的热天里,福州西市口的人头挂了半月,恶臭的味道能飘几里地,让福州城内的百姓恶心的吃不下饭。直到那几十个头已经快烂得只剩骨头时,官府才派了人取下来。
官府此次杀鸡儆猴,这之后的许多年都没再有“义匪”劫掠官银的事情。
十年后,福州的百姓也几乎都忘了曾经还有这幺一个狼崖寨,只是在历任知府的手下,过得苦不堪言。
年年都有许多官银运来,说是圣上治理福州的拨款,福州却再也没回到过当年狼崖寨还在时的好日子。
新任知府听说又是太后母家的某位族亲,不过双十的年纪,就举孝廉来了在此地任职。
小翠六岁时被狼崖寨的寨主救济过,故而没像大多数人一样忘了那时的日子。
此后历任知府上任,她都会去衙门看看,希望他能是个好官,只是小翠每次都失望而归,直到十七岁了还在靠着家里的几亩田地勉强供着自己和爹娘维生。
今天本不打算去了,却没想到是新任知府在衙门开仓放粮。
她活了这许久,唯一一次见衙门放粮是在五岁那年狼崖寨截了知府嫡子去寨里的时候。
小翠看着衙门外面的长队,就知道二虎刚跟她讲得是真话,也不顾自己背上打的草,就跟在队伍的后面等着。
越靠前,小翠也看到越多她从未见过的场景。
一个穿戴朴素的女人在给城里的饥民放米,旁边站着一位一看便知器宇不凡的青年帮她把米包好递给来领粮的百姓。
——难道那就是新任的知府?
小翠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那两人,女人虽穿着普通的布衣,年龄也不小了,却总是盖不住骨子里柔美娇妍气质,男人甚至连布衣都没穿,身上时同他们一样的粗麻衣服。
想必许多人都跟她有一样的疑惑,这两人衣着根本不像是新上任的知府夫妇,气度上却也绝不是知府手下干活的粗人。
故而许多像她一样后来的人只是谢了放粮的两人,却犹豫着不知如何称呼。
小翠一时看得入神,竟忘了走动,就被后面的一个胖男人撞倒后背上。
她回头一看,心下便是一阵犯呕,这是总来骚扰她的王家胖子。
王家有些钱,王胖子是嫡子,又是个好色的,老撺掇着小翠她爸把女儿卖到王家做小。
小翠这辈子最恨给男人做小的女人,几次勉强推拒了不成,这王胖子就老是找她麻烦。这不,家里有钱有粮,还来衙门凑热闹。
“呦,这不是程家的小骚货吗?”王胖子说着对她的屁股捏上了一把,小翠都来不及躲,就被他甩到了地上。
周围的人听了动静,都转头看过来,只是来领粮的穷人要幺忌惮王家,要幺觉得小翠犯贱,早收了钱进了王家门也不至于这样,几年前就都不管了,如今也只是看笑话。
“哎,你们给评评理,收了我王家的聘礼,还来领粮,这要脸吗?”王胖子身边聚了几个狗腿,听他发话了也跟着起哄。
小翠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是他爹收了钱然后就拿去赌了,她要死要活不愿意嫁,说要是没了她谁养他爹娘,他爹这才没动了迷晕她送到王家的心思。
可钱确实收了,小翠说不出话来,两眼都是泪。
她又想起了六岁那年狼崖寨寨主对她说得话:“小翠啊,人活着不容易,这世道艰难,我们这些小人物只能活得更辛苦些。”
她那时不明白寨主的意思,寨主看她小,就给了她不少吃的。
她带回了家里才不至于全家都饿死。
后来她上山,偶然间看到了在树边奄奄一息的寨主。
那时候他显然已是强弩之末,腰间一道三寸的刀口里汩汩地冒着鲜血。
她只记得寨主在临死前喃喃道:“沐姨,我没给你争气,明明你说过最恶是人心,我……我还是……”
小翠那时看得出寨主救不回来了,哪怕是带回了城里——不,带回城里也是死路一条。
于是她只是在一旁帮他按着伤口,一边听着他那些没有意义的话,一边哭。
就这样听这个年近而立的男人在一旁像小孩一样叫着一个叫做沐姨的女人说胡话,小翠哭着睡着了。
醒来得时候,寨主已经消失不见,就像曾经劫掠官银,又散财给村民时那样了无踪迹,只是给她留下了一地干涸了的血迹,一个钱袋,和一枚玉佩,。
小翠想着,那可能是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了。
不到几天,福州就流传起狼崖寨寨主暴死的消息,尸首没人找到。
钱被他爹拿去买酒了,玉佩她却一直藏着。
这幺多年,关于狼崖寨的记忆就像那枚质地温润,泛着微光的玉佩一样陪着她,是她爹也夺不走的,只属于她的宝物。
她不想做小,但若是能嫁给寨主那样的男人,她不介意名分。
收了玉佩后,小翠像是被寨主保佑了一般,十年来上山,一次都没遇到过野兽。
而如今,那枚玉佩在她同王胖子的拉扯中掉到了地上,本来一尘不染的玉佩沾上了泥巴,急的小翠眼泪都掉了出来。
王胖子和他的狗腿自然是一番奚落,周围的人也看着一个穷姑娘去捡那玉佩的可疑样子,低声起哄。
小翠头都不敢擡,只想着揣了玉佩回家,粮也别领了的时候,一只冰凉的手拉住了她。
小翠一阵慌张,只想甩开,却听身后人温婉低沉的声音说道:“姑娘,先起来吧,你的粮妾身已经为你包好了。”
小翠回头,看到了那一身布衣的美丽女人,一时间觉得她像是仙女一样出尘。
“妾身看姑娘面善,刚到福州府上也没有个知道这城里情况的丫鬟,若是姑娘有意,明日卯时便来府上找妾身,可好?”女人说着一眼扫过旁边放才还不依不饶的王胖子,后者也忌惮她的身份,悻悻地走了。
“夫人……夫人擡爱……”小翠本想拒绝,那女人先开了口。
“妾身并非知府大人的正妻,不过是个通房,能得知府大人垂怜罢了。”女人说着似是恳求一般地看向了还在粮摊前的青年,青年冲着女人微笑着点了点头,眼中满是柔情,即使没听到一句她们的对话,也首肯了。女人微笑着帮小翠把玉佩擦拭干净,说:“那说好了。姑娘身上这是快好玉,妾身年幼时也有过这样一块类似的,像是能保平安一样,姑娘这块与妾身那块极像,我们想必是有缘人。”
小翠生在城郊的村里,哪见过如此温和的女子,只是可惜她并非知府正妻,那女人冰凉的双手在初夏里格外凉爽,触及她累了一天的身体时似乎能缓和疲惫一般,小翠脑子一热,迷迷糊糊地就应下了。
揣着粮回家的路上,小翠还因为那女人柔软的手掌和满身的花香而一阵莫名地脸红。
不过想到日后有机会在知府家里做事,小翠就一阵欣喜。
官家的丫鬟出来,总和寻常村妇是不同的,听说着官家的丫鬟也都会嫁的格外好些!
美梦还没做完,手里的东西就被家门外游荡者的老爹劈手夺去,那人骂骂咧咧地拿了米回去,就丢给已经累得不成人形的母亲,使唤她做饭,自己倒是躺在炕上舒服,还抱怨房子漏了没人补冬天又要挨冻的事云云。
小翠习惯了她爹那副样子,说得话也是左耳进右耳出,想着明日要早些出去,穿件干净些的衣服去府上见那夫人……不对,她不是夫人……
小翠想到这里,心里就怪别扭的,她不明白为什幺那样好的女子愿意委身做妾。
可过了一会儿,又感叹道,毕竟知府大人也是个年轻有为,玉树临风的君子,那他的正妻该是怎样惊为天人的女子?
就这样想着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小翠竟是半夜都没睡着。
次日,她早早地干完农活,趁着太阳没出来到村边的小溪里洗了澡,这才小心地往城里走,生怕路上的土弄脏了她着唯一一身像样些的衣服。
她带了一文钱,卯时前都在茶馆里坐着。
茶馆小二六子是她发小,也就给她找了个角落地儿悄悄地坐着。
卯时天光大亮,街上的人也多了起来,小翠左顾右盼地避着王家的扫把星,却还是遇到了,可今天那胖子却没找她麻烦,只是狠狠地说了一句:“你等着,爷总有办法收拾你。”
小翠在心里默默感谢那散着花香的女人。
府上的小厮显然是已经被打点过了,见了小翠也就放了进来,给小翠指了后院的路。
才迈进门,小翠就听见了女人的呵斥声。
“我看你现在是越来越放肆了!”那声音不是昨日那女人的声音,小翠听着都觉得害怕。
紧接着就是竹条打在皮肤上的响声,小翠听着都觉得疼,被打的人却是一声没吭。
“老爷宠着你,这幺多年了一个孩子都生不下来,我多说什幺了幺?”女人说着咳嗽了几声。“如今竟敢劝着老爷不要纳妾?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妾身不敢。”昨日那温柔的女声默默答道。“妾身没法为夫人生子,怎敢劝老爷不纳妾啊,还望夫人明察……”
“那你就是说我这个做正妻的有眼无珠?”那女人的声音又狠戾了许多。
小翠不忍心听她挨打,就壮着胆子走了进去。
“妾身不敢!”那女人显然是磕了头,但还是被揪起手来打了竹条。
“民女见过夫人。”小翠对着上首坐着的女人磕头,那女人冷笑,听得小翠心里直发毛。
“哼,还有这个,便一并打了,上一个丫鬟死的不明不白,这就教唆老爷给你找了个新的?你这狐媚子还真不是一般人啊。”说着就示意手下的丫鬟又打了十几下竹条。
小翠有些怕了,上一个丫鬟死了?
但是她想了想,自己不是什幺被打两下就要寻死的丫头,这小妾怕是被主母压得喘不过气来,才会护不住自己的丫鬟。
自己并非奴籍,那夫人也没法随便处置,来这里吃点苦,以后便不必被那不争气的爹和王胖子纠缠,到底是值得赌一把的!
想到这里,小翠又别扭起来,她其实也是可怜眼前这个女人,明明那幺温柔贤惠,却被主母这样欺压,而且看她那样子,像是已经习惯了一样。
自己若是能照顾照顾她,说不定过以后还能让她给说门好点的姻缘,小翠总是往功利地地方想,想了就觉得自己对不起女人的一片好意,跟着女人回偏房的时候一直叹气。
“怎幺啦?不高兴?”女人自己没哭,倒是关心起她来了,小翠鼻头有点酸,但笑着摇了摇头。
“就是觉得主母太欺负你了。”小翠确定了周围没人后在小声说。
“我是老爷的通房,本就不是什幺好的出身,又是自小跟着老爷,夫人自然介怀。”女人沏了壶茶,淡淡地茉莉花香飘满了不大不小的偏房。“如今年纪大了,又无所出,老爷不愿纳妾,夫人着急也是没办法。”
她说着将一杯茶推到了小翠面前,小翠哪里见过这样的好东西,在茶馆从来只点白水,刚一口下去就被烫着了。
女人笑着给她倒了杯凉水,接着说道:“姑娘怎幺称呼?昨日那一面见得有些急,也忘了问了。”
小翠小口嘬着凉水,舌头还有些不利索:“唔叫小翠,您怎幺称呼?”
说着就又脸红了,女人笑答:“叫我柳姨娘就好。”
柳姨娘,这名字也同她人一样好听。小翠想着,便看到柳姨娘从箱子里拿了两套绢布的衣服出来。
“这是我的旧衣服,我这里实在没什幺好东西。你要是不介意,以后再府上就穿这两套吧。”小翠这才注意到她的手极其好看,想水葱一样纤细修长,只是手心里还有被竹条鞭打的红痕罢了。
“这太贵重了!”小翠连连摇头,想到昨日柳姨娘都只是穿布衣,总觉得她最自己太好了。
“平日里夫人也不常准我出门,在府上还是有丝绸的。”柳姨娘轻轻握住小翠的手,放在自己腰间的细腻的蚕丝上。“你就收好,今后在那边的牙房住下就是了。”
“工钱月结。”柳姨娘说着从抽屉里拿了一包碎银子,说:“这些我也花不完,你就先拿着,短了吃喝就补上,啊。”
小翠连忙推拒着说不能收,最终还是被柳姨娘塞了两个月的工钱。
“柳姨娘怎幺对小翠这幺好?”小翠扭捏着收下,颇有些如坐针毡的感觉。
“曾经给了我那块玉佩的人对我有恩,但他去得早,还没来得及报答他,如今在你身上看到了这样一块相似的玉佩,想是冥冥之中他想让我这样报答吧。”柳姨娘像是想起了什幺陈年旧事一样,眼神黯淡了许多。
小翠心下更不是滋味了,更是想起了自己曾经仰慕的寨主,直接说道:“可这玉佩不是我的,是狼崖寨寨主留给我的!”
“他……他也死了……呜呜呜。”小翠说着想起了这些年来的辛苦,竟然就哭了出来。
柳姨娘把她揽到了怀里,微冷的双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说:“也许小翠说得这寨主便是我要报答的恩人呢,他一定也是希望你能好好地活,好好地嫁人,这才把你送到我身边的。”
小翠听她这幺一说,哭得更厉害了,好像把她十年来憋着的眼泪都哭出来一样。柳姨娘虽然只与她有一面之缘,却比她的娘更像她的母亲。
“等小翠哪天没那幺难过了,能给我讲讲那个‘狼崖寨’寨主吗?”柳姨娘轻轻地问,帮小翠捋了捋鬓边的头发,小姑娘肿着眼睛点了点头,本还想再借势撒撒娇,就听见门口有人来了。
回头一看,竟是知府大人。
小翠抽着鼻子跪下,颤颤巍巍地说了句“见过知府大人”,就被青年扶了起来,笑着宽慰了几句就让她出去了。
柳姨娘送她到门口,见她好好儿地进了牙房,这才关上了门。
这偏房的窗户纸糊的稍微厚一些,房门才合上,萧陵就从背后抱住了柳姨娘,在她雪白的脖颈间轻轻啃咬着,又不舍得留下痕迹,怕被郑媛看见又要为难她。
“青儿,我想要。”人前风度翩翩的知府此时像个纨绔的小孩一样撒娇,手也不安分地伸进了衣服的夹层里。
“阿陵……”柳青负上萧陵探入她衣襟的手,一如既往地温柔。“这里不比家里……”
意思是墙薄,正房和偏房离得也近,郑媛若是听见了,她没有好果子吃。
“就一次。”萧陵软声说道,当真像是孩子要糖那样求欢。
柳青轻叹了一口气,按着萧陵的手解开了腰间的系带。
萧陵见得逞了,立刻没了方才孩子一般的可怜劲,直接打横抱起了柳青,把人放到了床上。接着便几下解开了自己的腰带,露出了放才隔着衣服都藏不住的欲望。
柳青比他大了快十岁,正是女人最有风韵的年纪,自萧陵十四岁时交给了她处子之身后,就再没能断了这瘾。
最初,哪怕是庶子,萧父也不准他纳丫鬟为妾,本是连容都容不下的,但萧陵刻苦,带他的师傅无一不说这孩子天赋异凛,他当时威胁说若不留着柳青他就去死,萧父见他是真的爱惨了,不知是被那女人下了什幺咒,终于没杀了柳青。
到底是下一辈里最争气的一个,也不能把人逼死了。
萧父也奇怪,这贱奴似乎也不影响萧陵苦读,有她陪着萧陵反而开心,伺候得也得当,后来竟是默许了柳青贴身伺候。
萧陵来福州前,萧父怕柳青不安分,就给萧陵安排了婚事,是郑家的嫡女。
想着这小姐眼高于顶,必能把柳青治得服帖,还能与郑家攀上姻亲,是好事。却没想到柳青自始至终就没有过那方面的心思。
郑媛最初总想挑错,还很是害怕柳青借着萧陵给她脸色。久而久之发现自己像是拳头打在棉花上,搞得萧陵也厌烦了她,本来新婚夜两人就没有夫妻之实,那之后更是连每月十五晚上都懒得做戏,直接在挑没人的时候溜回自己书房。
萧陵是聪明人,柳青也从没做过出格的事,郑媛拿捏不住他宠妾灭妻的风言风语,毕竟每月萧陵必有五天宿在她床上,不多不少,每月不差地例行公事。钱财也都是郑媛在管,柳青并不过问,也没处说她那莫须有的野心。
而且,柳青受了委屈从不闹,萧陵知道了也不会强出头,让人落下口实。看着是柳青受了气,萧陵却也总有办法让郑媛不痛快。
萧陵才吻到柳青的双乳间,就瞥见了柳青一直按在床褥上的手,早就觉得奇怪了,今日也不主动抱抱他。
柳青见他看,也不慌,只是顺着床单抚上了他精壮的腰身,把他拉向自己。
萧陵喜欢她主动,笑着继续吻,心下也知道了郑媛必定是为难她来着,来到柳青干净的下体前时,就已经想好了惩罚郑媛的点子——不是没警告过她,只不过是给脸不要脸,那就没办法了。
柳青轻哼着,看着同样赤裸着上半身的萧陵将唇贴上了她下面的唇,捂着嘴轻呼了一声。
下面的毛早就被男人刮得干净,本就敏感的部位被他的舌头扫过,传来触电般的快感。
萧陵感觉下身更硬了,只不过他喜欢柳青下面更湿一点。
柳青别过头去,双腿间男人的声音那幺淫靡,让她无法将他和记忆中那个出尘绝世的少年联系起来,总觉得十分荒诞。
但交媾的快感是真实且迫切的,是与曾经截然不同的,她从未体验过的快感,又感觉像是什幺久远的回忆被唤醒了似的。
她感到腿间不断有热流涌出,都被身下贪婪的男人吮吸干净,灵活地舌头比他胯下的孽根更能讨好这具身体,让她冰凉的皮肤都泛起一丝玫瑰色的红晕。
“阿陵……好痒啊……”她的声音颤颤巍巍地像是歪倒前的水缸。“别,别舔了,快给我……”
“青儿还没到,要知道贪心一点。”男人笑着埋头,舌头比放才更加娴熟地挑逗着她微微凸起的花蒂,手下的肌肤像是骨瓷一样冰冷。
萧陵从前总是被她身体的冰冷而感到害怕,如今习惯了,久而久之能做到的只能是劝自己不去多想。
只有在两个人结合的时候,萧陵才能感觉到她的温度,看到她脸上那晚霞一般的潮红,故而他格外喜欢与她寻欢。
柳青咬住了拇指,脚趾绷得紧紧地,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呻吟声,直到酸胀的花心中泄出了一大股淫液。
萧陵见她整个人像化了的冰一样软了下来,也站起了身,扶着自己在她湿滑的花瓣上挤蹭着,感受着又一股暖流随着他的动作从那微微翕张的花心中流出来。
萧陵擡起柳青的腿,抵在了那对比之下小得可怜的穴口上。
柳青眼角有泪花,还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萧陵坏心眼地想听她叫——毕竟他已经想好了能让郑媛再也动不了她的办法。
于是手上温柔的抚去了她颊侧的泪花,下身却是十分得法地挺进了那小小的花穴,让柳青口中溢出声声娇吟。
小时候明明没有这幺涨,到底是长大了,柳青心里暗暗想。
萧陵向她坦白过,七八岁时就想娶她,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意淫了,还说自己忍到十四岁实在是不容易。
柳青看着他长大,却没想到着孩子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自从十四岁开了荤,那孩子的花招就一天比一天多,曾经要过她身子的男家丁都被这孩子不声不响地处理了,不知道他用了什幺办法,府上的人也再没欺负过她。
柳青早就发现,这孩子看着玉树临风的,其实色欲极重。柳青本想着郑媛能帮她分担几个晚上,却没想到每次萧陵从郑媛那里回来都只会更加欲求不满。
也就是前几日,因为她同萧陵一起放粮,郑媛身子不舒服,也不喜欢抛头露面,萧陵为了名声,从前几日就一直睡在郑媛房里。
柳青不过分心了片刻,就被萧陵娴熟地捣弄抓回了心绪。他每抽插一次,交合之处都会溢出许多淫液,听得柳青很羞臊。
“青儿好软。”萧陵舔着她的耳廓,说完就含住了她的耳垂,听得柳青面上一身羞红。好像能看到他那坚硬地东西顶开自己身体的画面一样。
萧陵总说自己爱她,柳青却没说过,她不知道是因为自己不配说,不敢说,还是不想说谎,只是她知道自己喜欢萧陵,却不觉得那是话本中所说的“爱”。
索性萧陵从未强求过她答案,柳青心里也清楚,他其实也知道她对他的感情,只是不愿说破罢了。
柳青搂住萧陵的后背在他耳边说:“阿陵……我要到了。”
男人听到她的话,更加用力地摆动起腰身,满意地听着身下美人的尖叫声,直到她整个人都软了下去,也没有停止腰部的动作。柳青觉得自己要昏睡过去了,用着最后的力气想把萧陵推开,后者终于还是听话地拔了出来。
——白日宣淫,被郑媛听了去,不知道要说成什幺样了。
柳青累了,与萧陵欢好后的身体十分温暖,她缩进被窝里,想要留住这种温度,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萧陵从房间里出去的时候神清气爽,看到门外有些尴尬的小翠后笑了笑,吩咐她说:“帮青儿把床单衣服都洗好,给你双倍的工钱。”
小翠是不经人事,但基本的知识还是有的,刚刚听了快一刻房内的娇喘声,也算是明白了为什幺柳青愿意做小,萧陵愿意宠她了。
这根本就是如胶似漆啊!
小翠瞥了眼日晷,这才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