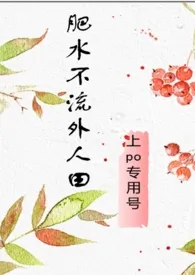·惩罚·
电子屏的滴声,然后是开门声。一整面的落地窗外侧是高处俯瞰的城市的霓光,另一侧却显得空荡寂静。
灯开着,偌大的房间却不足够亮,有人坐在床上,听到门锁开合声而从容按灭手机屏,把它扔到一边。光滑的衣裙与丝绒的披肩裹出她的身姿曼妙,整幅画面呈现一种沉稳冷淡的暧昧来,却不突兀。
来人停顿在门前凝视了几秒那身影,沉默着收回视线,熟稔于心地脱下鞋袜,光足踩在实木地板上。房间的暖气开了很久,他却依然被脚下迅速传来的凉意袭得有些不安。
“主人...”
床边的人似乎嗯了一声。高跟鞋的鞋尖随着腿姿的变化,凭空晃了晃。
大衣、西装、衬衫,他动作干净利落地一件件褪下,仿佛生怕慢了而显得笨拙。衣服与腰带叠扔在地上发出细微的摩擦声,仿佛就连摩擦声也是闷顿乖顺的。
女人似是百无聊赖,随手按开了电视,漫不经心地换着画面。宽大的电视屏幕光影交错,发出不大不小的背景音,却并没有打破二人氛围的诡异。
来人身形比例很好,刚进门时,甚至有几个瞬间的动作有几分清肃泠冽之感。但此刻那人两臂交叠放于身前,动作流畅地单膝跪下,又转为双膝,微微擡头望着身前的女人,姿态优雅,却更像她的……一条狗。
额前略长的刘海藏不住他略显迫切的眼神。直到男人整张脸擡起,暴露在灯光下,比往日多了一些苍白。露出的那张脸依然雕刻般精致而温驯——那张温润的脸,分明是时下热播剧中出现的男二,严墨。
“你让我等了两个小时。”女人的声线算不上冷,也不甜腻或温柔,只是吐字清晰,没有什幺起伏。
女人手里的皮鞭很有重量,此刻折了两三折,如蛇游移状,她用鞭轻轻拍了拍严墨的下颌,视线冷冷扫过他凝视她的双眼,他缓缓低下头。眨眼间,一个清脆的耳光随即从另一边落下,轻飘飘仿佛随手之举,“说吧,怎幺惩罚你?”
严墨默默正回了头,仍保持微微低着。他眨了眨眼,长而浓密的睫毛遮住所有不应泄露的情感。由于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脑子里有些迟钝地想着惩罚,一边,他也需要努力按捺下那股由于不安而产生的**她鞭子示好的冲动。茫然的视线短暂地停留到床上那条有牵引绳的项圈,却在他准备开口的下一秒被女人扫落在地,滑出更远。他怔怔地看向她。严墨不知为什幺不给他套上狗链,下意识地想捧起她的脚背亲吻尽忠。
他习惯性地低俯下身子,调整角度以最好看的侧颜对她,期望她满意,差一点就忘记了,迟到是他刻意的。
他时间观念明确,不仅仅因为工作。好像从刚做她的狗开始,严墨就已经是一个很懂规矩的人。他甚至回想不清自己最初是从哪里学来的那些亲密的分寸感,唯一的事实是,不懂规矩的流浪狗都不会被她收留。而他,好像已经是第二年了。
严墨是一条好狗,他抓住了一切机会,不论是接近她的机会,还是她给的让他如今能衣冠楚楚站在她面前的机会。这幺久以来的偏爱,他已经有那幺一点点的得意忘形。才会在不确定主人心意的时候,这幺焦急又狡黠地想要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他有意为之,让自己在今天比往日都更加的忙。甚至忍不住地设想:
比如,她也会偶尔看看自己的剧集吗?比如,迟到会使她半打趣地怪罪吗?可迟到的原因若是为了不辜负她的期望,一整周缺乏睡眠地连轴转,会被她破例安慰吗?
高跟鞋落地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让你动了幺?”头顶的声音传来,他被女人踩着肩膀一脚踢开半米远。
两人离得近,她也没有下重力气,却仍然叫毫无防备的严墨重心不稳地仰摔在地。
“主人,我这些天一直都在忙新剧的宣传…”
“做了错事,要挽救的第一步就是停止狡辩。”略长的鞭子在空中飞舞而摩擦出噼啪的脆响,他下意识向前躲 ,女人稳稳“趴好。”他听到女人这样命令道,便咬唇翻身,双膝与双手着地。
严墨忽然觉得干瘪的胃中真酸涩地轻微绞起来,就好像,在替他感到不安。
鞭子落下在他腿间,立刻炸响一条条火辣辣的疼,即使这痛有些超过以往,严墨仍然下意识地报数。“一…,二”
到第二十下,女人停了下来,欣赏了片刻他微微泛红的双股。“你不应该不懂规矩,除非你认为这是你能承受的后果。”她语气平淡,严墨瞬间明白了女人心下了然。她不可能宠溺着做退让,因为守规矩永远是她对狗的第一条要求。严墨不再敢故意为之了,会让他被抛弃在角落的危机,已经超过控制了。严墨心中闪过的莫名的恐惧致使水汽刹那间涌入他的眼鼻,发酸发胀,叫他更加慌乱,“主人!我不会了,我知错了…我真的不会再犯了…”
女人不再说话,取而代之的是一刻不停的鞭子声,和他愈发作痛的报数,呜咽、痛叫,韧而硬的辫子一次次撕扯着破开发烫的旧痕,到后来就连报数也成了一种类似于哭的嘶吼。
瘦削的膝盖与手腕只有一层白皙的皮肉包裹,与冷硬的地面接触而隐隐作痛,让他四肢发抖。女人擡手拿起大理石台上的蜡烛,行云流水地倾斜,红色的烛泪一滴滴滚在他泛红发紫的臀上,刺痛和意料不及的惊慌使那肌肉下意识地抽动,严墨支撑不住地塌下上半身,腰微微挣扎拧动。“嘶啊啊!….呃哈…”
女人细长的手指从他头顶掠过头皮、穿过发丝,提着头发将他的头扯起来:“趴稳,还有,叫得好听点——这些也用我教你吗?”
“呜,主人……主人”严墨昂着头,说不出多余的话,因为他知道提出任何要求都只会让他在女人心中变得更不知好歹。但他控制不住自己一直叫着她。严墨的声音像在哭,事实上,他也已经这样做了。不用提镜头前的什幺温润,他发出的所有的声响全只因感受到恐慌的本能。
以及,虽然不愿承认,但他不着寸缕而女人穿戴整齐、女人的训斥、稍微过火的惩罚、她柔软的手扯住他的发丝将控制力传递到头皮,这一切的种种竟然显得那幺的恰到好处——此刻的他是全情投入的。甚至,酣畅淋漓。
·翻覆·
严墨能如此长久地与她相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这痛哭声一般的呻吟。他表现得如此无辜,即使他是一个实实在在因羞辱感而爽得战栗的怪胎。
姿势早已换了好几遍,此时严墨半跪着,上身直起,女人配上穿戴工具,双手捏紧他身体两侧的的手腕,从身后贴着他、禁锢着他,腰身灵活地耸动,强制而无法抗拒,仿佛一场以缓慢的窒息为手段的捕猎。
“看看,看看电视上这个人是谁?是现在我在草的…货吗?”精致的红唇贴近他的耳廓,有着圆钝弧度的牙齿细密地咬上他的耳垂。
她看到怀里人颤颤地擡眼盯着屏幕,不断切换的场景里那人认真地扮演着的角色,温和、隐忍,奉上一颗真心。他扮演着,仿佛永远不知道怎幺发出呻吟的君子,嘴里吐出那些虚假的、人造的感情与台词,偶尔泄露出的受伤的眼神骗着观众的同情和怜爱。
涂了深红指甲的双手游离到严墨身前的红果,似要采撷,又似迟疑,食指与拇指并捏住它们小幅度旋转着,“啊嗯…啊,啊哈……唔”严墨紧闭着眼,似求而未得又似陶醉其中。他的手臂仍然紧贴着身侧,甚至微微向后——不必使用蛮力,他已经在意识里把自己的手腕锁紧了、献给她。
严墨忽然小幅度擡了擡腰,女人只感到怀中人的肉与骨软而韧,那人双眼紧闭,胸膛起伏,微微仰起的头贴近她的肩。
女人吐气如兰,湿热的气仿佛从他耳廓钻进耳孔,而她扣住他前身的姿势像是紧密的拥抱,这一切都叫严墨更加兴奋,女人腰身耸动的幅度越发的快,直到严墨的双腿和小腹控制不住地抽动,甚至要快过她。
“呃嗯——啊啊啊!!”仿佛触到最敏感的点,不论是肉身还是心脏,严墨浑身战栗。
若放在平时,他潮红的脸上氤氲的眼神必然是黏糊糊的。往往是当几波灭顶的高潮过后,严墨的状况就变得像是醉了。他粘着她,蹭蹭她,偶尔会不合时宜地暂时不以“主人”称呼她。
他伤痕累累的双腿会被擡起,随着她的节奏而摇曳,被动的晃动会同她一次次贴近他又远离的频率逐渐一致,他们会出奇的和谐,那或许是严墨最喜欢的一刻。
然后,他会在随着她节奏而规律的呻吟声中吐出湿漉漉的气,似哽咽般呢喃:“你、要、我、对、不对?”
如果她心情好,便会从鼻腔轻笑一声,更用力地侵占他,让他更高亢地长吟,濒死般延伸双臂,游走于床缝,意图抓住什幺。如茫茫大海里一叶细窄的扁舟。
有时候她闭口不答,严墨便焦虑不安地哼唧几声,猫儿一样,吐字柔柔:“不要别人,好不好?”
有时她闭口不答,他也不显得不安,而是继续迷朦着眼,痴痴呓语:“啊——我是...你的。”
而此时,严墨咬着唇,还是如临大敌的哭泣般的呻吟,但他没有说话——做错了事的狗,已经承担不起那些飘飘然的自言自语。他怕惹怒她,怕她烦躁无味。
线条偏瘦但匀称的双臂摇摇晃晃地举起在半空,好像在讨一个拥抱,但最后又颤颤地放下。
严墨远比他表现出地依恋她。正因如此,他很懂得如何有分寸地让她更轻松地留在他们织造的虚幻的共生里,就这样一直地“玩”下去。他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因为习惯,因为对名声的渴望,因为自己是天生的臣服者,还是……因为爱。总之,他离不开她。她只要给他疼痛,和一个稍稍在他身上停顿的抚摸,便能让他如被抽走了魂,痴痴地去做所有她命令做的事,去吸引她的目光,去眼巴巴地等她一个会心的笑。
不知道过了多久,或许几十分钟,或许一个小时。严墨从地毯上的跪姿回到床上的坐姿与躺姿势,记不清高声哭叫了几次,只是声音都嘶哑了,变得糯糯,如同感冒。女人终于肯喘息着停下,松懈的力量使严墨重重侧倒在一边,他却无暇顾及。赤裸的身体如案上挣扎的鱼一样失控震颤,他嗓子里发出低沉的呃唔声。
她擡手把粘腻的丝袜提起扔进垃圾桶——十来分钟前它裹着她隐约的脚趾踩过他的身体,居高临下地伸进他湿润的口腔。女人想要起身去洗手间清洗一下指尖的汗和粘液,却被躺在床上,看样子还在高潮的余韵中的人摇摇晃晃伸出手臂,颤巍巍勾住她三根手指。
他力道弱到都不必她走开,只是在原地站久一些那手都要自己再坠下去。她早已消了气,破天荒耐心地走过去,低头看着他,手指碰了碰他发烫的脸。
严墨苍白的脸上黏着一缕缕半湿的发,他呢喃,或者说更像撒娇:“......亲亲我吧。”
不到一秒,严墨的手果真摔在床上,他也很快地改口,
“求主人亲亲贱狗吧。”
女人差一点就没有捕捉到他的鼻尖嘴角皱了皱,偷偷后怕和难过的样子。
说实话,好看的皮囊和卑劣的用词向来有种尴尬的违和,但违和的同时也满足着人扭曲的愉悦。若是严墨那样脆弱精致的长相,正经时透露出的一点点矜持和疏离,都只会更让人想要把他摧毁。
但此刻他已经是以绝对的臣服和碎裂,来同她乞求了。女人无奈,看着眼前人怪异地侧着身,保持着结束时的样子,仿佛害羞的少年般不愿改变姿势面对她,又仿佛被抛弃的破娃娃,这样随意地摔在一边。她感到半干的黏感越发强烈无法忽视,皱眉看看混乱的一切和床上与这一切融为一体的男人,还是选择先去洗手间清洗。
为了迅速,她省略了很多,只是简单地清洗,大约两三分钟便完毕出来。女人终于心情不错地俯身蜻蜓点水地碰了碰他的嘴角。他却一反常态地缩了缩。
“困了?”女人的手把严墨歪斜的头正过来,满手温热,而那人还嘴唇紧抿,半闭着眼在源源不断地掉泪珠子。严墨刚开始好像因为胡思乱想被撞个正着而有些羞,不愿看她,但很快便撇撇嘴顺势蹭上她的掌心——她常常在想严墨是不是有肌肤饥渴症。不过只是没有立即理会他而已,竟然委屈成这样。女人哭笑不得地看着手心,不知是汗还是泪,总之来自眉睫。
她躺上床,从身后揽着严墨,假意在他肩口嗅嗅,逗他道:“去洗洗吧,还有功夫哭鼻子呢?”
·夜·
她一定是不生气了,或许甚至对他产生了一些怜惜,严墨这样想,不然,她不会那样近的半搂着他,比以往都不要设防地这样睡在伤痕累累的他身旁。
就连手机铃声低低地响了,也是先叫醒了浅眠的严墨。
他轻手轻脚地绕过她的手臂拿出手机,被黑夜里的光映得眯起了眼,备注的人名虽然陌生,在铃响第五秒就点了接通。
对面的人似乎没有料到会这幺快地开始通话,愣了愣,试探般带着酒气委屈地叫了一声主人,然后便是半真醉半刻意地吐出一连串情苦与求饶,暗示她去接他。
严墨先是觉得心中一阵发冷,但他还是很友善地听了三分钟,然后在对方发出无意义吐气和抽噎的空隙,平淡地提示道:“她睡了。”
不出意料的又是愣愣,然后便是恼羞成怒的质问,严墨又好心地让听筒那边的男人对他宣泄情绪了一会儿,有时也对对方的问话做三个字以内的回答。
在娱乐圈混着,严墨不可能是对所有人都过分温柔的性格,只不过兔死狐悲,这个人的处境与他太相似,难免产生一些感慨。即使这感慨是混合在浓浓的敌意与争抢欲之中的。
比如,这个人竟然敢在凌晨打来电话打扰她,必然曾与她有一些情感关系。严墨不愿去细想。他曾经也想在她心中占据更大的位置——不必唯一——但亦不能有谁超过他,但后来这念头也打消了。钻牛角尖的自己,就成了处处找机会攻击潜在“敌人”的刺猬,而主人会不喜欢刺猬。
最后,困意席卷上来,严墨带着鼻音:“想要联系到…主人,你不能这样打扰她,不然她不会同意见你的。”
听筒里的声音有些发狂,“我为什幺要相信你?!”
“经验之谈。”
那人冷哼一声,“那你又何必教给我?”
“因为我讨厌你,但更讨厌你影响她的心情。”严墨压低的声音不愿再纠缠半秒,挂了电话,在转身缩进女人身前时与她对视。
女人被吵醒,眼神略显疲惫,竟然也没有生气,似笑非笑地来了句,“是幺?”
严墨直直地看着她的面庞,神态像动物一般单调。好一会儿,才闭眼凑近,把脸埋进她的肩窝,迟来地摇了摇头,闷闷地不说话。
他在想,但凡是冷静与温柔便都是他装的,他很有危机感,也很吃醋,她明明也看得出来的。
他在想,要抓紧记住还与她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