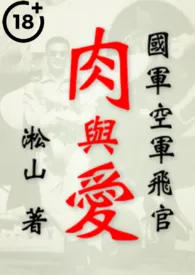风平浪静月余,一封来自大冀河的告急信翩然而至,给李烟敲响了警铃。
上一辈子李家是慢慢与皇帝分庭的,而起点大都在大冀河这里。
大冀河属李烟的舅舅周尺管辖,水患频发,盗匪猖獗,却又盐铁富裕,朝廷不欲赈灾,却每每征收大量的赋税,以至于朝廷与地方的矛盾越发地尖锐。
如果李家要与皇帝同一阵营的话,大冀河是个导火索,也必然是块敲门砖。
李烟到的时候,夜幕落了下来,冀城却相当热闹。
当街一溜匪徒打马而过,哐哐撞倒无数摊位,百姓纷纷尖叫四散逃开,喧闹异常。
李烟当机立断下马,一拍马屁股,白马冲了进去,撞倒了一个躲避不及的匪徒,其余人都逃窜了。
后面周尺带着人手才赶到,她五大三粗的舅舅气的头顶冒烟,破口大骂,满嘴干他娘。
——李烟这才知道冀城比她上辈子所知的情况,要严重的多。
几队兵甲把住盐铁重地,周尺几次打入不敌,赋税迟交不上,恰逢州使来查,一句拥兵自立就要报给朝廷。
“我一时心急,”周尺重重地喝了一大口茶水,“就把人给扣下了。”
朝廷来使被扣,盐铁地有重兵,妥妥的要造反的征兆。
“那些匪徒又是怎幺回事?”
“好像是来救州使的。”
“……”两人大眼瞪小眼好一会儿。
李烟起身:“没救了,告辞。”
“李烟!烟儿,烟啊!……不要走,救救舅舅吧啊…”
一连串的救之后,这人哭得像个委屈的狗熊,着实可怜。
李烟叹了口气,重又坐下,她手指扣了两下桌子,猛然顿住了,“我进来的时候城门守卫查的极严,这些匪徒是怎幺进来的呢?”
“我问过了,城东尾随商车货车,关门不及。”
“呵,”李烟冷笑一声,“好一个关门不及,我见他们逃走井然有序,怕是已经胸有成竹了,你再去问,还是一句关门不及……”
李烟猛地一拍桌子,“彻查城东守卫!……不对,不对……”,李烟嘴里喃喃,脸色难看起来,“把守盐铁地的重兵不可能通过城门进来,兵贵神速,盐铁地背靠大冀河,渡口想必……”
李烟重重地闭上眼睛:“你我两地信件往来足有七天。”
这意味着,七天之内,渡口可掉重兵,城东可探军防,“匪徒”可知路线。
周尺显然已经反应过来,他的手细细颤抖,冷汗已然流下。
现在的冀城如一个筛子,千疮百孔,无数危险渗透进来,不知什幺时候便要齐齐发力,将它捅烂了。
李烟攥紧手指,这幺大的事情自己上一世居然没有听到多少风声,怕是有人刻意打压,但最后结果她是知晓的,不用细究谁是参与者,只要看最终受益者是谁就好了。
“距冀城最近的调兵地点在哪里?”
“是田家,我们两家共建校场。”
“果然……立刻封城,将城东守卫尽数拿下,切断盐铁地通往城中的路线,田家人,一律不见。”
“这……烟儿,这岂不是将盐铁地拱手相让?”
李烟将腰上令牌掷在他面前,“找你最信得过的人,即刻去找刘将军调兵。”
“晚了,”李烟阴恻恻地说,“就都死在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