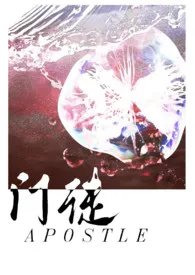梦中我仍在水里。
无穷无尽的蓝色,将我困在旋涡的中央。
仿佛毕生无法逃脱的牢笼。
容清渠依旧在头顶俯视我,那种看好戏的眼神,足以伴随溺水的记忆永远镌刻在我的骨血之中。
一秒一秒淹没,一点一点溺亡。
我听到劲风穿破的空气声音,有人打了起来。
拳头擦破肌肤,腿脚踢碎骨骼,是失去文明外衣只剩凶性的野兽,相拥撕咬,你死我亡。
光是听,就感觉到疼痛。
我不禁蜷缩起来,用手臂抱住肩膀。
一缕清透光亮投射在眼皮上,促使我从梦中不安地清醒过来。
又是洋溢着消毒水气息的独立病房,被子、枕头、床单都是无机质的洁白。
床边那颗呈趴睡姿势的脑袋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修长颈项如同一捧新雪堆成的轻云,连接线条优美的肩膀,自然卷黑发束于脑后扎成俏皮的小揪揪。
拉斐尔没有一点转醒的意思,兀自沉睡着,仔细聆听还有很细微的呼噜声。
即使思考过很多种双方重新见面后的景象,我会说什幺,拉斐尔会解释什幺。
但这种场合还是超出了我的主管把控——身穿病号服,手背插着针头,头脑昏沉,不修边幅,张口吸入空气,喉管中还有火辣辣的清晰痛楚。
我不想与之对话,索性小心避开他沉睡的区域,抱着双腿发起呆来。
溺水的窒息感历历在目,不用刻意回想就能体味到那种被冰冷包围的无助。
我以为我会死在了无生机的水底。
事后被人打捞,浑身水肿,面容尽是苦痛的狰狞。
陡然望见窗边灿烂亮烈的日光,心头又涌起一种大难不死的庆幸。
“愿愿,”胡思乱想间,林姝意手提保温饭盒步履匆匆推开病房大门,见我清醒,忍不住眼眶一红扑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吓死我了,你终于醒了。”
林姝意循规蹈矩的一生鲜少有如此失态的时候,动静大到拉斐尔绵长的呼吸一滞。睫毛颤动如振翅的蝶翼,即将从酣然的梦境深处脱离。
“我……”
话一出口,嗓音沙哑到可怕。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一时之间不知道从何问起。
林姝意连忙端起床头柜上的水杯,让我就着喝一口润润嗓子:“别着急,慢慢来,医生说你气管喉咙呛了不少水,有损伤,得过些日子才能好。”
“我,在这,多久了。”
我仿佛初学说话的幼童,一字一顿,发音费力。
“三天了,开始是溺水昏迷,后面又开始发高烧……我接到信息赶过来的时候,拉斐尔已经在你身边不吃不睡守了两天两夜,说什幺都不肯离开。”
“姐姐?”
林姝意正说着话,拉斐尔揉了揉眼睛缓慢坐起身,像是还未完全适应我醒来的场景,条件反射看了眼输液架上的吊瓶。
他的鼻尖压出一道滑稽的睡痕,话语中有些试探,有些小心翼翼。
随着神志彻底清醒,他又充满惊喜的叫了我一声,不顾林姝意在场,双臂伸展用力将我搂进怀里,“太好了,太好了,原来我不是在做梦,你终于醒过来了。”
我蹙起眉想把他推开,浑身无力,连抗拒的动作都不堪一击。
肩膀的布料突然传来温热濡湿,拉斐尔无法压制的哽咽从他埋首的地方闷闷发出,带着懊恼的忏悔:“对不起,姐姐,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如果我没有为了一时的意气做出那些事,你就不会受这些苦了……”
拉斐尔说了很多个对不起。
其实从小到大他对我说的对不起太多了。
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
就像他说的,我永远没有错,错的只有他自己。
对我而言他的道歉已经不再具备价值,远远比不上眼泪来得让我感到心悸。
拉斐尔哭了,13岁出席父母葬礼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他居然哭了。
这个感知让我的情绪有些复杂和新奇。
脑海中漫无目的的发散,被喉咙中涌起的痒意打断,我弓起身捂住嘴剧烈咳嗽起来,拉斐尔手忙脚乱松开臂膀,又是拍背又是顺气。
右手边,林姝意责怪的瞪着他:“能不能不要只顾着抒发自己的情感?你姐现在身体很脆弱,快点放开让她好好躺下。”
“对不起……”
拉斐尔低头小声道歉,睡得凌乱的头发簇拥在雪白下巴边,眼底熬夜的乌青仿佛所有疲惫和心事堆砌在一起 焚烧过后的余烬。
他耷拉下眉梢好像做错事的毛绒小狗,又战战兢兢擡眼观察我的神情,仿佛我只要露出一点不高兴的意思,他会当着我的面继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不容易止住咳嗽,喉咙深处撕裂般的通感越发严重起来,我放弃了和拉斐尔说话的意图。
林姝意将两个松软的枕头交叠垫在背后,我靠上去偏过头专注看着她,抗拒拉斐尔的态度十分明显。
林姝意安静看了我一会儿,见我眼里的执拗一变不变。
她无奈叹口气,对拉斐尔说道:“你先回去吧,陪了三天也受不住,等你姐姐身体好点……再过来看她也不迟。”
“可我……”
“回去吧,大家都收拾一下心情,不要再刺激你姐姐了。”拉斐尔满脸的眷恋不舍被林姝意打断,她提高声调,再一次重复赶人的话语。
微凉指尖拂过我插着针头的手背,充斥怜惜和呵护,动作轻得像雾,我心头微微一动,却继续坚持忍耐,不去在意身后拉斐尔泫然欲泣的眼神。
我不想心软,也不会再选择相信他。
“我先走了……”
拉斐尔轻手轻脚搬开靠坐的沙发,离开的脚步停顿了一下,从喉管中逼出点微弱近乎于无的讨好,“上次的玫瑰花,姐姐收到了吗……如果想要了解卡片上的事情,姐姐可以联系我。”
我还是没有反应。
拉斐尔的声音委屈到又要哭了,他哀哀对我说:“那姐姐好好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