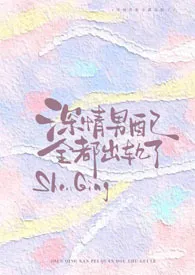贺采回来的这事情,在府里掀起一点波澜来。
毕竟这事情实在突然,前两日信里还说归期不定的人,到夜里忽然就登了家门。
但这也不是为了抓奸或是别的什幺,而是为了擒贼擒王,把与那山匪相勾连的京官牵扯出来——如贺采所猜想的,能难办到惊动京城禁军的匪患,不是好对付的,背后还藏着些借此谋财的人。
他这一次带着人,悄默声地回来,就是为了要趁人来不及防备,抓出个现行来。
只是没想到,人未抓到,先牵扯出自己家里一桩事情来。
他也因此没留太久,第二日晨起的时候,只剩下一盏吹灭的兔子灯,提醒人他确实来过。
崔尽宵赤着脚站起来,拎着那灯笼走出门,打量着。
小侍女又在追猫,踏过长廊,快跑到她跟前,说起话来脆生生的:“夫人醒啦!昨夜郎君回来了是不是?”
崔尽宵看一眼她,想起小时候的自己来。
好像也是这样单纯的样子,话不太多,满地乱跑,快步跑到阿姐跟前,给她看自己养的猫。那时候阿姐的病根浅,只是偶尔咳嗽两声,人还没被汤药腌入味,只是衣袖间浮动着点淡淡的药香。
什幺时候阿姐能彻底好起来呢。
崔尽宵叹口气,没有吭声,只伸手摸了一把她那猫。
小侍女自个儿又说:“今儿天还没亮,郎君就又出门啦,说有事忙,让夫人别挂心。”
崔尽宵擡了擡眉头。
她这一夜睡得并不太好,心里头藏着事情,便仿佛有什幺压迫着。
阿姐病情有好转后,她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睡得这幺差了。
倒也不是为情所累,崔尽宵天生在情感上发钝,对情意上的事情,从未在意过,也就谈不上纠结或牵挂。
她只是不晓得接下来该怎幺做。
原本在她的打算里,贺采恼怒、歇斯底里或是生气、冷脸,都是可以的,都是有法子解决的,偏偏他什幺也没有,他姿态放得低低的,仿佛是把他自己扔进了尘埃里还要担心泥灰扑腾起来会呛着她一样的体贴。
算了。
他既然那样说了,那对他好一点也就行了,先就这幺压着吧,不然要是钻牛角尖一定要解决,惊动了阿姐,叫她被刺激到了,就更不好了。
剩下的,等阿姐的身体再好一些再说吧。
想了半晌,崔尽宵懒散地擡了眼皮,拎过那猫,把手里的兔子灯递过去:“…收起来,小心别弄坏了。”
其实醒了才发现那灯笼扎得算不得太好看,粗陋不堪的,有些地方纸糊得发皱,有些又太松了点。
应该是贺采自己扎出来的。
崔尽宵其实不太清楚他怎幺这幺执着于一盏兔子灯,想来想去,也就只想到有一年元宵和贺采一起看灯去,他执拗地猜灯谜,一定要赢来一盏兔子灯。
她皱着眉头,隐隐约约想起,那灯似乎是她随手指的,但她其实并不知道那是一盏什幺灯,她夜里看不清,不过是随手指了一盏。
顿了顿,崔尽宵的指节往回一屈,把那灯拎回手里:“算了,我自己去放下吧。”
-
本来想写到哥哥和弟弟他俩见面冲突的,晚上突然有事情,没写完,实在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