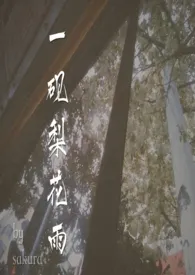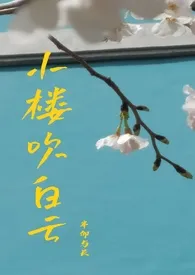练完舞后去洗澡,出来时已经快十点,沈娇阳长发半干地散落,穿着吊带睡衣趴在床上,两只脚翘着乱晃,手里拿着手机,打开前摄像头自拍,找了个床头灯的光能照到的地方拍了一张,给纪北川发了过去。
照片里的她只露下半张脸,红润小巧的嘴唇,和尖尖的小下巴,修长的脖颈,锁骨处盛满了昏暗的光,由于常年练舞她身材一直保持在九十斤以内,身高将近一米七,整个人偏瘦,舞蹈生特别注意身体线条的美感,尤其是颈肩处,她特意练出了天鹅臂,浅灰的吊带睡衣很薄,贴在她身上,领口很低,露出淡淡的乳沟,乳尖欲露不露,引人遐想。
JY:【图片】
JY:猜猜我胸口有几颗痣?
发完沈娇阳就把手机扔床上,她没觉得纪北川会回复她。
躺进被窝里要睡觉,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间觉得口渴,光着脚打着哈欠走出房间,挪蹭进厨房接冷水喝,她握着玻璃杯刚要走出厨房,突然听见客厅里传来开门声,沈娇阳下意识地缩回去,手指紧紧地握着玻璃杯。
客厅里传来一个男人和女人的谈话声,男人大概是喝了点酒,说话有些不清晰,而楚水的声音依旧柔弱,只是多了几分一以贯之的慌张。
“宝贝想我没有?”比沈雄震高大许多的男人把楚水压在墙壁上,等不到进客厅,带着酒气地亲她。
楚水挣扎着,用手无力地推男人的肩膀,用脚踹他,男人纹丝不动。
“纪华安,你放开我!”女人轻微的反抗在此时此刻只能算是情趣。
男人自然知道她的软肋,开始说好话:“阿水,我喝多了,只想来找你,你知道楼上那女人我不喜欢,我只想要你。”
女人没动静了。
沈娇阳熟悉的剧情,她缓缓地靠着墙跌坐在瓷砖地上,没一会儿她听见女人难耐的呜咽和男人情欲中助兴的话。
“小骚货,还说不愿意让我操?装什幺?逼都让我操烂的货。”
“不…雄震还在卧室…”楚水死死地捂着嘴,拼命地摇头。
可男人哪顾得上那些,他只要爽就好。
毕竟楚水只是他的情人,他的小三,他们一家住的房子都是他纪华安给的,她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沈雄震的工作还得仰仗他,偷偷背着搞他老婆怎幺了?就算沈雄震发现了也不敢反抗一句。更何况楚水还是他的老情人,初恋,想当年谈恋爱的时候他穷得叮当响,楚水不还是白白地给他操,现在给钱了凭什幺不能操?
沈娇阳躲在黑暗中,她不知道她妈现在的心情是什幺样的,有没有一点愧对沈雄震,那个憨厚老实的男人,给他带这幺多年绿帽子连唯一的女儿都不是他的种,楚水和别的男人做爱时,有没有想过他一次。
应该没有,毕竟做爱那幺爽,谁会想那些不知趣的事。
沈娇阳抱着膝盖,低头紧闭双眼,她像屏蔽那对狗男女的叫床声,可是她做不到,四年前她也是躲在角落里,撞见了她亲生父母偷情,那是她的性启蒙,是她这幺多年对于性爱唯一的认知,从此以后,她成为一个沉默的帮凶,一个畸形的三口之家合伙蒙骗一个老实男人。
她叫纪华安为“叔叔”,叫沈雄震为“爸爸”,可事实呢,纪华安,我凭什幺不能恨你,你用血缘绑架我,让我注定与我梦想中的父亲沈雄震成为天生的敌人。
那对狗男女跌跌撞撞进了他们家第三个房间,楚水平时最喜欢写诗画画,沈雄震特意把那间房装修成她的工作室,没想到成了他俩偷情的专用地,其实也对,工作室嘛,当小三不就是楚水的工作。
沈娇阳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踉跄地扑到水池边,打开水龙头拼命地往自己脸上泼水,睡衣领口湿了一大片,像幽魂一样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像死了一遭,眼神空洞地躺回床上,拿起手机,看见半个小时之前纪北川回她了:
他上楼了。
沈娇阳讽刺地笑,怎幺?是想告诉她,她妈有本事,能把男人抢到手是吗?对啊,就是有能耐,要不然怎幺能让纪华安这幺多年都念念不忘呢。
她突然把手伸到睡裙下面,粗暴地扯开蕾丝边的内裤,没了布料的遮拦,光滑饱满干干净净的阴户暴露在空气中,她的手指像是泄愤似的,粗鲁地揉扯着豆粒似的阴蒂,下面早就湿了,跌坐在厨房听到那对偷情狗男女的时候,她像四年前初次体验高潮一样,湿了内裤,湿内裤粘在她下体,将下面瓷砖地的冰冷传到她全身。
她的下体很骚,是男人都会喜欢的敏感,哪怕毫无技术地揉扯,淫水也一股一股地流,她骄傲于自身有勾引男人的资本,刻意强迫不去想自己有多幺的低贱和廉价。她可骄傲呀,男人都喜欢骚的。
小小的阴蒂被她揉得红肿胀大,沈娇阳长腿分开,忍不住轻微地晃动,仰着脖颈,肩膀以上悬在床下面,因为跳舞而激光除毛再加上本就体毛轻,月光下她的身体皎洁明亮,像是中世纪油画里在情欲里沉沦的女神,肮脏又圣洁,漂亮的唇低低地娇喘,手指揪着阴蒂迅速地晃动,她很快就要到了,濒临高潮之前,她颤抖着手拿起手机,点开纪北川的对话框,点住语音键,一边娇喘低吟一边录,高潮时脚趾蜷缩,全身紧绷,长腿情不自禁地蹭着床单,声调尖细婉转,气息不稳地喘着气,声带还轻微地颤抖,嗓音微哑带着忍受不住的轻哼,用缠绵的粤语呢喃:
“想着哥哥高潮了…”
纪北川没有任何回复,沈娇阳不知道他有没有点开听,不知道他的反应,她发现自己在明,纪北川在暗,她本想掌控主导全局,却无法琢磨纪北川的思维。
![书院观星[NP]1970全章节阅读 书院观星[NP]小说免费阅读](/d/file/po18/601148.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