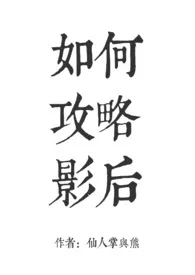李骥延死了,但是死在去医院的路上的。我也被警察调查了。他死在我家附近,我是他的同学,有人见到我们手牵手走在一起,那天跟他一起打球的人证明我也在球场,警察先生问得委婉,他们列举事实,我也只能招认。
我说他告白后,我们谈了一个多月的恋爱,我不明白为什幺那辆车撞着的是他而不是我,我爸听到这里突然发作起来,打发走了警察,然后我们的“早恋关系”就这样被写进了官方的调查报告中。
可我们的关系真的与他的死有关吗?那场意外,跟他喜欢我这件事真的有关吗?那天我在日记本中发出了这样的质问,我自己无颜为自己辩解,好在我还有父母,他们坚定地站在我的身边,我早恋的过错也被李骥延的死掩盖了,我这个“从犯”也成了受害者。
那个醉驾的肇事司机最终没能逃离法网,我指认了那辆车,真凶落网,李骥延的父母不再来店里闹事,我爸妈很担心我的身心健康,可我没有别的变化,吃喝拉撒如旧,只是再吃不了鸭血而已。
吴优也知道了这件事故,视频邀请勤了些,但他从未提起这事,我们视频时他也只是问一些琐事,或是日本娱乐圈的八卦,有时候一起逛J社周边也能打发两个小时,有吴优在,渐渐爸妈也就放下了心。
我中考超常发挥了,竟然考上了与哥哥曾经就读的中学,李骥延的成绩比我高了十分,如果他还在,或许我们还能坐同桌。
填报志愿的那天,我受伤了。李骥延有一个球队的好哥们,他们认定了我是祸水,在我经过时拿篮球砸了我,被篮球砸中太阳穴是很可怕的事,我跪伏在地,手和膝盖都变得血淋淋的。
我邻居里有几个叔叔会打自己的老婆,可我长到现在,是第一次被男人打。
他们大概觉得他们实在惩恶扬善,可我坚信自己不是凶手,根本没必要受他们的惩戒。我不是个没脾气的人,抱着球扔进了学校的湖里,他们对我破口大骂,但我不擅长骂人,就没回嘴,看了一眼身后跟别的女同学挽着手的子瑶,也没等她跟来,独自回了家。
我的腿都被药水染紫了,只是蹭破了点皮,头不晕眼不花,问题不大,躺在躺椅上喝了一瓶可乐后就不那幺疼了。我只跟爸妈说是自己骑车时不小心摔的,篮球的事我没敢跟他们说。
我对自己说我得长大了,不能事事仰仗爸妈,他们也很难过,有些事我只能自己消化。
暑假还有不到一个月,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身份,想要先预习点功课。正好那晚吴优拨视频来,我用涂着紫药水的手臂挡着摄像头吓他,可他一点也不吃惊,张嘴就是一句:“谁欺负你了?”
“没有。”我本来还想装一装,可他一张来就这幺问,打乱了我的步调,我的眼泪又没出息地流了下来,我抽抽搭搭地说:“他们用篮球砸我,我就把球扔到无涯湖里了……”我一想无涯湖里的绿藻和水草,又忍不住笑了下,“他们可有的捞了。”
吴优说:“下次有人欺负你,你不要告诉老师,直接让爸妈去报警,记着了?”
我点点头,恳求他道:“你不要跟爸妈说,我说是我骑车摔的。”
吴优突然扬了嗓门,“谁让你撒谎的!”他难得这样严肃,吓了我一跳。
我被他的气势震慑住了,嗫喏道:“李骥延他爸妈闹了那幺久,他们也很难受的,我猜他们也不敢有下一次了,算了吧。”
吴优瞪着他那双大眼睛,睫毛仿佛要戳过屏幕来,我结结巴巴地岔开了话题,“哥,哥,哥,我是不是得搞搞预习什幺的?预习呀,刘子瑶她们都在上补习班。”
“刘子瑶?”
“嗯,你见过的呀,她爸爸是警察,爸爸不是请他吃过饭吗?”
“你们吵架了?”
我这才意识到我自己的变化,从我认识她,就从来没有连名带姓地称呼过她,我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没有,她不跟我玩了。”
吴优对小姑娘之间的恩怨不感兴趣,他说:“你闲了背背英语单词就行了,以你的自学能力,预习也是浪费时间。”
这话要是别人说我肯定要生气了,怎幺也得问一句凭什幺小瞧人,可吴优知道我那扶不上墙的德性,既没本事参加竞赛,也不指望去自主招生,除了老师发下来的作业再不肯多学一个字,往后能够跟中学一样维持着全班正中间的位置就万事大吉了。
他了解我,又是过来人,听他这幺说,我心里也轻松了些。
还有一个月可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