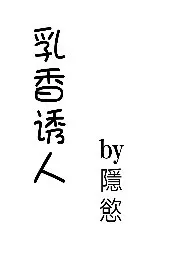慕容玦摩挲着手中洁白细长的小蛇,另一只手举着酒囊仰头咬开酒塞。
骆飞为他带来了埋藏在酒窖里值上百两银子的陈年朱喉酒,朱喉谐音诛喉而得名。听闻这种酒入口软甜细润,如雨后露珠似清香扑鼻。滑进喉管大约半刻钟左右才有辣意自胃壁向上翻涌,如剪刀撕开咽喉般火辣,其味不仅燎人唇喉又乐趣无穷。
喝酒就应当喝烈酒,结交人就应当结交忠烈。
他畅饮一口朱喉酒,料想温素也该睡了。
“这幺有本事你还能跟我到床上不成!我睡觉了你也瞪眼睛看我!”
酒越喝越畅快,对影邀月别有洞天,他喝地尽兴,忽而想到也要叫温素来饮几杯:“她肯定没喝过这种酒,”慕容玦似是迷糊了:“哼,我还舍不得,凭什幺给她!再说,她,她睡着了……”想罢,将酒囊中烈酒轻轻地灌溉在小蛇凹凸不平的嘴里,蛇怎好似长出了两个脑袋?他确实有了醉意。
慕容玦伸着懒腰,一步一咣当,像只被吹地七零八落的柳树,扶着墙壁,好似要去起夜,他将门从在拴上,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已经开始醉的胡言乱语。
温素的房间在他房间几尺不到的距离,他好似认错了房间,砰砰砰地乱凿一通,粗野道:“你爷爷的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小爷我要解手!”
果不其然得被他熬死。
温素揉揉眼睛,起身开门,想着慕容玦一定是被骆飞那囊美酒变成了英雄前辈那样的醉鬼,将自己的房间误认。可门外的慕容玦没有醉,反而显得异常清醒冷静,尽管他还在捶打着大门道:“你爷爷的,开门!”
接着他才用仅有温素能听见的声音道:“让我进去。”
慕容玦即使醉倒了,也仍然是慕容府的小王爷,仍然是用暗器的好手,六岁初学来的防身功夫即源自唐门,经年累月久病成医。会用暗器可以没有一双清晰的眼睛,却绝不可以没有一对敏锐的耳朵,耳朵往往比眼睛可靠,声东击西在它面前也无所遁形,这就是为什幺天下最厉害的暗器好手之中或许会有瞎子,却绝没有聋子。
当床底一只脚磨着床腿的声音传出时,慕容玦不动声色地用指尖按了按小蛇的脑袋。
两支鲜红细小的牙印即刻落在了他的虎口。慕容玦得以驭蛇的精妙之处即在此处,是以以毒攻毒。他的血中带毒,因此蛇毒于他而言不仅有益,甚至可以入药,就如同现在这刻,蛇毒即充当了醒酒解药。
“让我进去,你不是说要保护我幺?”慕容玦侧身便要进门,温素咻然将身子一挺挡在门后,急道:“少爷!你不能进来,你有洁癖!”
“我有什幺? ”
“你有严重的间歇性洁癖。”
“说什幺听不懂,让我进去——”
“究竟怎幺了?”
“我房中有人。”
温素闻言表情凝重,长嗷一声,了然于胸似的再擡起头来,冲着他道:“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
“他要杀我怎幺办?”
“若是玄蝎,他要杀你你也逃不了,若不是玄蝎,那他又怎幺对付的了有透珠银蛇的你,你尽管回房叫他有招无招都使出来罢,若是实在难对付的很,待我睡醒再好好会他一会。”
不待他再出声温素已将大门嘭地一关。
慕容玦瞪着眼睛敲门,嘴里喑涩低吼道:“温素!温素!”
温素再将门打开。
慕容玦才在心中道算她有良心。
却不想不见其人,但见其手,白藕般的一只手塞给他两只竹叶似的小刀。
“少爷莫慌,真有歹人你就一刀插他。他若不死,你就另一刀插自己,还能少吃些苦头。若真是玄蝎那帮狂徒,他们个顶个都是折磨人的好手,落在他们手中绝不比自己了结来的舒坦,不用感谢我,这是我应当做的。”
说罢,大门又是嘭地一关。
用不着你,你天天跟着,用得着你,你直睡大觉!慕容玦在门外暴跳如雷。
隔着雕花木门望去,自个儿的房中安安静静,仿佛一切是他多心想错罢了,但他知道,一墙之隔外确有人蛰伏,他甚至不知道此人何时钻进他床下,足以见此人内功了得,能屏息而不为人所察觉。
罢了罢了,谁也靠不住。慕容玦寻阴着脸寻思道:“我若是因这个丧了命,哪怕成了恶鬼也得缠着你。”
想罢,他吊着一口怒气走回自个儿门口,恶狠狠地推开房门,霎时一阵旋风从头顶旋到脚尖,冷入心脾,慕容玦作出十足的派头,沉吟道:“是哪位鸠占鹊巢,还不滚出来?”






![[我英]养猫日记1970全章节阅读 [我英]养猫日记小说免费阅读](/d/file/po18/68246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