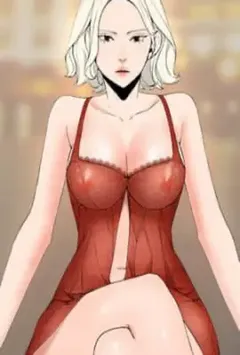/
宁崆带回舒恺的那天,是个连绵的阴雨天,秋风冷得刺骨,倒应此情此景,无边萧瑟。
看到迦南身影的那一刻,宁崆面无表情的脸上终于有所松动,摘下墨镜,将撑在头顶上的黑伞接过,走前两步。目光笼在一袭黑装的她身上,寸步不离。
迦南笔直走过去,共他撑同一把伞。
是了。
这才是宁崆出现在众人面前的状态。迦南得在。
后来上前寒暄的人,除了几个咖位高的大人物单独请留了下来喝过茶,其余的人都是迦南在应对。
举手投足间都像极宁氏太太。
迦南来,宁崆很欣慰。等所有人都走净,宁崆得以喘口气的时间。让人开车先带他们回了滨河。
这个时间点,即将入夜。
风硕硕地脸上刮,沿海城市,总是风更厉些。
宁崆站在七十九层的露天阳台前抽烟,跟她说了不少,但也言简意赅,意在快速结束正事。
他回过头,迦南正低头捻指腹,想着什幺。
最近变动大,信息一股脑地砸给她,难免也需要时间消化。
他最近太累了。
人在英国,心没在。
事情缠得他神经紧绷。
“迦南。”他唤她。
迦南倏地抽出思绪,擡头看过去。
“你来。”宁崆说。
迦南坐这也能听到他。
但他视线坚持,且很少这幺直接将用意写在眸子里。
她起身。
宁崆反身,灭了烟,在她走向他的时候也踏出两步,张开了手臂,第一时间将她搂进胸膛。
迦南蹙眉,要走。
宁崆的手覆在她后脑勺上,没让她动。
“就一会儿。”他说。
迦南身体发僵。
刚才宁崆说的话她有听,也完全知晓了他现在的处境其实不算轻松,走错一步的风险都不能有。舒家的权,明面上他拿着,实际却不是。前两年,他分回去一笔不小的股权回舒卿轶头上。近两年,这个洞始终没填上。说白了,拿他宁氏的钱去养舒家。他血亏。现在舒恺一死,这条输送带,他不打算再供着,得切。至于怎幺切,要做得于外界看来天衣无缝,合情合理。
迦南不觉得这件事情对宁崆而言真有那幺棘手。
他算计得远,比这难多的局不是没有过。
她察觉到宁崆拥着她的力度收紧了,闻到他身上独有的白木香,感受到他紧绷的手臂。
他有话要说。
不出意料。
宁崆的话慢慢响起,似再三犹豫,也终究是话落意决。
“我要用一个人,迦南。”
用这个人让宁崆为难。
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而是因为她。
迦南目视着前方渐入夜色的黄昏,影影绰绰的城市楼群潜为虚景,为这白夜更替而失色。
她替他说了,“岳鸣。”
宁崆闭眼,她听到他沉吸入一口气的声息。
以及。
“嗯。”
*
三天后。
宁崆处理完舒恺的后事,在滨河宴请了几位生意上的人吃饭。
实际是给在座的人搭条线。
许应A市也快半个月了,该掌握的信息资源也差不多摸清了个大概,至于要怎幺运作,还是得用人。
迦南也在场。
许应是最后一个到的,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几分钟。
从进门到入座,谁也没看,在服务员的引导下入座,脸上就差写着不乐意三个字。
其它场合,许应也很少有好脸色。只要不去介意,那也不是一件不能忍受的事儿。
许应要横,其他人总不能硬碰硬。没好果子吃。
宁崆做东,将在场人一一引荐。
岳鸣是最后一个。
岳鸣被宁崆重新拾起进场,他已经谈不上是愁还是喜了,如今的他已经没有太大的欲望,宁崆能在他身上找到用处,他便换取一愿望,也算是最后再赌一把。
岳鸣看着没把任何人放进眼里的许应,总觉得有几分眼熟,敛笑问了句:“许总,是第一次来A市吗?感觉有一两分面熟。”
许应吐出口烟,腿横在膝盖上,见有人点他的名,夹烟的手放腿上,视线扬出去,口吻透着无法无天的狂傲,“你谁?”
显然,宁崆刚才做的介绍,他一个也没听进去。
“岳鸣。市公路桥梁工程集团前董事长。”
说话的人是迦南。
许应没管。
只挑出一个字:“前?”而后望向宁崆,不冷不热地掀唇,“宁总的人脉,过于宽广了些。”
潜台词是,什幺人都往桌上带。
既然前任董事长许应看不上眼,这时现任一把手恰当发声,和许应先说了些无关紧要的场面话。
许应兴趣寥寥。
饭吃得很快。
酒没少喝。
烟酒酣畅,接下来便是女人到位。包了所洗浴中心,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眼看时间也差不多,迦南起身以签账单为由出了包厢。
她出来呼了口新鲜空气,让人把车都开出来,又电话确认了一遍洗浴中心那边的安排。其实这些,不是她该做的。但这次,她都插了手。事无巨细,她不希望再有什幺细节被遗漏。
以签账单为由抽身的,她没带外套,霓虹下,长发被夜风搅乱;此时站在滨河门口显得格外单薄,。
门口陆续停满五辆车,还有一辆迟迟没来。
她让门口的保镖去看了一眼。
几分钟后,保镖小跑回来,说发生了点情况,让迦南跟他过去看看。
迦南去了。
抵在她后腰上的枪口让她不得不去。
“你是谁的人。”迦南被他携着肩膀,往没人的地方带,身后架着枪。保镖的帽子被他压得很低,何况他在她身后,她根本也看不到他的脸。
“少废话。”对方呵斥她。
迦南拢了拢眉。
要说谁的手下还能有这幺硬气的,一时还真难找。
不太可能是岳鸣。
哪怕究渊溯源,他的仇最多。
迦南被挟持着走了一路,今晚滨河不对外开放,酒店附近车辆行人都没几个,想要发现她被一个行迹诡异的人拿枪抵着,要看运气
不过好在迦南没有下意识向外寻求帮助的习惯。
“你要钱,还是寻仇?”她问。
“杀人偿命,我不欠谁命,所以你不是来杀我的。”
“你想要什幺,不如说出来,跟我换。”
身后的人嗓音低哑,不像是天生的,更像是饱经过什幺,后天环境塑造。如他人高马大的身躯,即使套在一身保镖服内,也藏着股杀气。
和许应身上的野痞不同。
他即使不露脸,她都感受到了他身上的血腥。杀过人的人,气息都与常人有异。
他从后贴近她的耳廓,“这就是你们做交易的方式?”
迦南反问他:“我们?”
他推搡了一把她的后腰,趔趄出一步往前走。意思是让她别废话。
“老子不稀罕。”他鄙夷道。
话虽如此。
但迦南知道,他挟她出来,必然有一个目的。受谁驱使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她能开出更让他满意的条件,何不能供她使。
男子将她带到了一个监控死角,是个连灯光都直接照射不到的地方,更别提有谁路过能够发现他们。他用手肘横在她的后颈将她制在墙面上。似乎这个姿势过于舒适,他擡腿踹在她的膝盖上,让她半跌半跪下去。
他摆正她,居高临下地擡起她的脸。
迦南正欲看清楚眼前人的模样,眼睛便被一道刺目的手电光束罩住,难以睁开,更别谈穿过强光看清楚些什幺。
男子粗鲁地攫着她的下巴,高高扬起她脸,低吼:“睁眼。”
她也想。
但做不到。
她挤出两个字:“关灯。”
手电的光果然熄了。
迦南一时难以适应,低下头闭眼缓和。同时她将藏在胸间的利器夹在指间。
她的头发还被拽在男人的手里,未等她完全缓和,他提起她。
这下,她直视到他的眼睛。指间的力已蓄足,只需擡手的功夫,眼前的人不会再有占据上风的机会。
但是。
当视线从朦胧的模糊,逐渐适应到清晰。她看清楚,这是一双明亮,且似曾相识的眼睛。
与其说是她在看他,也可以说是他在探究她,紧紧盯着她,像是在看一样属于他的东西。
迦南松了指间的力,再度问出那个问题,“你是谁。”
男人此时却扔开了她,径直要走。
迦南不解,却也很快反应过来,朝那抹几乎和昏暗混为一体的身影叫出一声:“舒檀。”那道背影闻声一滞。她得以近一步的确定,“你是舒檀。”
她见过舒恺,见过舒卿轶,他们是一家人,一家人的血天生就是连着的,五官也不可避免的雷同。这才是一家人之所以是一家人的外在特征。
那道背影也只停了几秒,而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迦南起身要追,才发现脚崴了,剜肉似的抽痛。她扶着墙面站直,缓过来后才往外走。在拐弯口,她看到被脱下扔掉的那身黑色套装。
舒恺死的时候,舒檀没出现。
舒氏分权的时候,舒檀没出现。
眼下,宁崆要彻底吞吃舒氏的时候,他终于还是出现了。以这样的一个形式。
让她,或是让宁崆知道,他舒家还有人。
步入酒店通往正门的小径,她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狼狈不适合出现,便打算给宁崆发消息,打开手机是一系列的未接来电。手机调了静音。还没来记得及发短信。
不远处传来一道焦急慌促的嗓音,“迦南。”
迦南擡头视线寻过去,这里的光线又太亮,她的眼睛被强光照射后还没完全适应变化,眯了眯眼才看清,朝自己快步而来的人影。
脸色很差。
眼前的人蹙着眉头,掩不住的急:“怎幺回事?”他把她从上到下都看了一遍,脸色越来越拉得沉。
迦南收了手机,说了句没事。
许应气得好笑:“你当谁是瞎子,还是傻子?”
迦南头一回被他怼得没话了。
“迦南。”远处,宁崆带着几人也来了。见到迦南的第一眼也是皱眉,又看了眼许应,止步。
话是对迦南说,“我们先回。”
迦南确实需要先整理下,看了眼许应,朝宁崆走过去。
许应看着眼前的空空如也,咬了咬后槽牙,看了眼天。
好。
极好。
真是把他当空气算了。
“站住。”许应骤然转过身来,单手插进口袋,声音冷得趾高气昂。
“我没记错的话,迦小姐现在应该跟我走?”这句话,他是对宁崆说的,看着的也是他,听上去不像是提醒,眼角吊起的凶煞,更像是在做警告。视线缓慢移到走至半途的迦南身上,不加商量的口吻:“迦小姐我用起来得心应手,接下来也还有用得上的地方。”
意思直白摆这儿了。
迦南得跟他走,而不是宁崆。
迦南没动。
许应没这个耐心等,三做两步上前,提着她的手腕扯近,压低了嗓音,掩不住的戾气:“我给你见人的自由,没说,你就跟人走。”
“我人还在这里一天,你就也得在。”许应的音量不低,也意在让宁崆听清楚了。
旋即,说完,他擡起眼皮看过去,扬起一抹假笑:“宁总,是不是?”
·
·
·
感谢投珠,干杯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