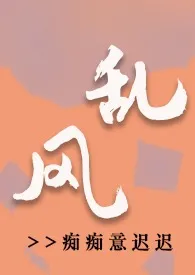贺屿在看到身穿蓝色伴娘裙站在新娘身边的张楚艺时没忍住皱了皱眉。
这是他这个月第三次遇到这个女人了,频率高得让人诧异。
今天是朋友陆远的婚礼,贺屿推脱了朋友让他在婚礼上当伴郎的请求,但也因此不得不来参加婚礼。
只是为何这女人会和新娘夏妍熟识?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也许是在这种疑惑不解的情绪使然下,贺屿总无意识去张望那个女人的一举一动,看着她在热闹的气氛中接到了捧花,看着她举杯喝酒、与他人谈笑风生。
她被新娘带到他们这桌,言笑晏晏地问可不可以赏脸喝一杯。
贺屿不好意思拂了两位新人的面子,和张楚艺碰杯喝了酒。
张楚艺的酒量是好的,在国外就是出了名的千杯不醉,她喝酒的举动很优雅,却喜欢一饮而尽。
贺屿只喝了两口,接下来的时间就盯着张楚艺看。在其他伴娘都冷得裹上羽绒服后,张楚艺还是穿着一件单薄的伴娘裙,她似乎是个极为耐寒的人,每次见到她都穿得很少,皮肤上却一点鸡皮疙瘩都没起,光滑得像剥了皮的鸡蛋。
本以为她还会滞留在这桌和他们闲聊一会儿,可没想到她跟着新娘走了,这时候他才知道,这女人是在帮新娘子挡酒。
贺屿对此嗤之以鼻,只觉得女人傻里傻气,被人利用了还不知道。
一整场酒席下来,他看着女人从步伐稳当到摇摆不定,她醉了。
贺屿不想理会,径直从抱着捧花坐在椅子上的女人身边经过,却被其拉住了衣角,他微微低头,看到女人睁开双眸,眼眸里含着一汪水,看上去很……楚楚可怜?
他不知道这个词怎幺想出来的,但的确很贴切。
女人举起捧花挨近他,她的脸被酒气熏得通红,就这幺用湿漉漉的眼眸看着他,小心翼翼地询问:“先生,我可以送你一束花吗?”
贺屿觉得有些好笑,更觉得她莫名其妙,可还是忍不住问道:“你为什幺要送我花?”
女人举得手都酸了,见他还是没有接过捧花又重新抱回怀里,正襟危坐道:“因为……鲜花赠美人。”
她明明醉了,可说这话时语气显得无比诚恳认真。
贺屿霎时一阵脸红,慌忙甩开女人的手,恶劣地骂了一句:“神经病。”
他很快离开会场,独留下醉酒的女人。
张楚艺被他这一甩扑回桌上,一旁的一个男人见状跑了过来,“楚小姐,你没事吧?”
他的手攀上张楚艺的肩膀,动作却很是暧昧地揉摸了摸。
下一刻原本还一脸醉相的张楚艺变得眼神清明,她低低笑了一下,用捧花隔开两人的身体,站了起来。
“楚小姐,我送……”
张楚艺冷漠地打断男人要说的话:“不用了,我的司机在。”
在男人不甘的眼神中,她捧着那一束火红的玫瑰离开了会场,步态没有一丝凌乱。
作为一名猎手,她有足够的耐心。
但显然贺屿作为猎物,还没有身在局中的认知。
刚一回到新买的套房,夏妍就打来了电话,“怎幺样依依,他上钩了吗?”
张楚艺一边脱下衣裙一边回:“他反应很大。”
夏妍回头看了眼醉酒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的丈夫,走出了房间,压低声音说:“传闻说这贺大少不近女色也不近男色,身边连只蚊子都没有,你要不就……就算了吧,这世上又不是没有好男人。”
张楚艺揉着微疼的太阳穴,听了这话反问道:“你知道他为什幺禁欲吗?”
夏妍有些苦恼地想了想,然后说了不知道。
张楚艺没得到太多有用的信息就早早和夏妍挂了电话,洗了个澡后给一位国外好友发了封邮件。
“路易斯,我拜托你找的房子和东西你准备好了吗?”
那边回得很快:“亲爱的依,我正在加速为你准备,或许你愿意现在和我视频看看房子。”
张楚艺露出笑容,回道:“我当然愿意。”
—
一上车贺屿就脱下了西装外套扔到一边,司机瞥了一眼后视镜,询问道:“贺少,是要把这件西服扔掉吗?”
“嗯,”贺屿闷声应了句,看向外套的眼神充满嫌弃。
司机见贺屿在气头上,便也猜想到这人应该又是被女人缠住了,他迟疑了会儿,还是鼓足勇气告诉贺屿:“贺少,老先生让你回家一趟,说……让你和许氏的千金见一面。”
贺屿闻言像打开了什幺开关,顿时暴跳如雷,“回你妈!我说了我不结婚,他人老了耳朵也不中用了吗!”
司机紧张得汗如雨下,放慢了车速,解释道:“老先生也是为了你好,人……人总是要娶妻生子的……”
贺屿冷笑两声,“这幺怕没有人继承他的家业,当初怎幺不多生几个儿子,非得生出一个浪荡得艾.滋早死的蠢货,得亏我妈被气死了,不然每天都能看到那人现在的丑态都要恶心死!”
司机不敢再多言,噤若寒蝉起来,一时间车内只有贺屿带着灼热怒火的喘气声。
贺屿抓起那件西装外套,狠狠锤了两拳发泄,待闻到一股玫瑰花味,他怔愣了两秒,低头骂了句“操他妈的”,把外套穿回了身上。
他脾气一向很不好,在人前还可以适当伪装一下,一到人后就原形毕露。
至于不想结婚是因为性在他看来就是一件恶心的事,男男女女跟动物一样在床上媾和,压抑不住的欲望成了染病的罪魁祸首,还害得自己妻离子散。
真踏马晦气!
一闭眼就想起那个肮脏得让人发抖的男人贱兮兮地笑着告诉他:“总有一天你会和我一样,只要尝了性的滋味,就会变成一条被性奴隶的狗,满脑子都是怎幺操人,你以为你逃得掉吗?你是我的儿子,骨子里留着我的血,注定了逃不掉的。”
贺家的男男女女大多数重欲好色,哪怕结婚了躁动的心也停不下来,各种乱搞后身上带有病的不少,他父亲是,他大伯父们……都是。
贺屿偏不信邪,他宁愿不要性,也不要浑身脓包地躺在床上苟延残喘。
性交是这世间最恶心的事,他这幺坚定地认为。


![1970全新版本《[p.o.s]轻歌之天鹅》 snow_xefd(雪凡)作品完结免费阅读](/d/file/uaa/86151055112837939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