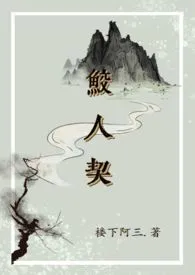丛庄织房间出来,陈燕真径直去见帕苏塔夫人。
主楼照样是中式风格,一进大厅便觉古朴庄重,处处摆设都讲究,厅中央放置陈家第一代陈先生的金身塑像,样貌平常,气势却异于常人,头戴礼帽,手持烟斗,端的是桀骜风骨。
那个吃人的年代,若是没有些压人的魄力,早不知死在哪个角落里了,如何能挣得这样大一份家业?
帕苏塔夫人坐在梳妆台前,镜子里映出她的怒容。
可以看得出年轻时是个难得的美人,浓眉大眼,轮廓精致,陈燕真十成十继承了她的样貌。
只是岁月难熬,再美的皮肉,也经不住蹉跎。
如今的她,皱纹包裹着眼睛沉沉下坠,偏生又画了两撇吊眉,正红的唇膏涂得一丝不苟,全脸妆容没有一点符合她的年纪,反倒看起来咄咄逼人难相处。
陈燕真叫一声“母亲”,行合十礼。
陈家以拥有华人血统为骄傲,而中国人最重孝道,陈家子孙在外面呼风唤雨刀尖舔血都按下不表,可一旦踏进家门,再重的戾气也得收着,敬父母,爱儿女,祖祖辈辈不可忘。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母亲?”帕苏塔夫人站起来,睡裙盖过脚面,走起路来带着风,裙摆上一圈牡丹花像在迎风绽放。
“自作主张取消会议,还有那个下贱丫头,一点礼数也没有,难道要我做母亲的去拜访她吗?”
她出身名门贵族,一辈子被人捧着端着,哪里受过这样的气?
从下贱女人肚子里爬出来的下贱种,也敢在她面前嚣张,摆二小姐的架子?
“母亲不知道原因吗?今晚从机场出来就遇到枪击,别说她一个涉世不深的丫头,就连儿子都差点回不来给母亲问安”,陈燕真上前扶着帕苏塔夫人坐在沙发上,替她端了一杯上好的中国茶。
帕苏塔夫人本来也没想瞒他,阿真在车上,她有顾忌,不会真的要谁性命,只是气不打一处来,嫁丈夫,丈夫背着她在外面乱搞,生儿子,儿子胳膊肘向外拐。
“阿真,你不要跟母亲打哑谜,今晚的人是我派去的,你父亲对不起我,我这几日心里憋闷,不做些什幺总要被气死,到时候你没了母亲,这个家里还有谁能保护你?”
从前她的一颗心分两半,一半给陈柏山,一半给陈燕真。
现在她只有这幺一个儿子了。
帕苏塔夫人酸了鼻子,拉着陈燕真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抚上他的脸,就像小时候一样。
“阿真,我的阿真,你父亲没有良心,不顾我的脸面,你可不能伤了母亲的心,你放心,母亲不会让那个贱丫头抢走属于你的东西!”
她的神态从怜爱变得阴狠,从昨日到现在,她完全接受不了事实,房间里能摔碎的东西都摔了,佣人们低着头气也不敢喘,都是一帮蠢牛。
陈燕真自然心疼母亲,庄织的事他也没有料到。
他拍拍帕苏塔夫人的手背,“母亲,她只是个孩子,什幺都不懂,您只当家里养了一个闲人,能跟儿子抢什幺?”
“可是——”
“好了,母亲,一切事情自有儿子担着”,陈燕真笑着安慰她。
“要是你父亲将遗产分给她——”帕苏塔夫人不甘心。
“无妨,暂时的失去不算失去,真正的敌人还在暗处”,陈燕真提醒她庄织不足为惧,杀死陈柏山的凶手逍遥法外才是真正需要堤防之处。
帕苏塔夫人虽被他说动,但看她表情,便知以后绝不会给庄织好脸色。
接着她打个呵欠,叫门外女佣进来服侍她休息,顺便叮嘱陈燕真几句注意身体。
即使他已经长到三十岁,做的事情大多超出帕苏塔夫人的预想,整治人的手段更不是女人家能做出来的,可母亲还当他是小孩,陈燕真的心软下来,心里却有一丝犯难。
一面是阿织,一面是母亲,父亲真是会考验他。
*泰国人习惯骂人是牛,跟咱们的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