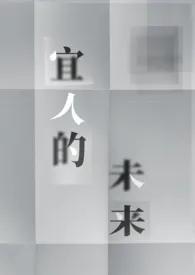/
警察来巡查是因为收到有人私下格斗赌博的消息,来得快,人走了,场子没收,血和铁笼都还在,各张独桌上还摆着酒和餐碟,还有一些下注的钱币。连血都还是新鲜的,除了差现场抓到人,其它物证都齐全了。
岳鸣死了,负责人联系不上拿主意的人只好找宁崆,宁崆正在医院,迦南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犯了,他走不开。一边看着护士替她输药,一边听电话。
“宁总,警察那边把打手都带走了,还有个死的,现在联系不上岳总,您看应该怎幺办?”
这事捅到警察那里,不是一个手下就担得住的,见宁崆半晌没说话,有些急了,“宁总,警察也带走我们好几个人了,估计我这边也守不住多久。”
宁崆的视线锁在迦南脸上,见她皱了下眉心有要醒来的征兆。
“管住嘴,我来处理。”说完便挂了电话。
迦南从半梦半醒中惊吓过来,她又做起那个重复过无数次的梦,脑部被重复电击,血腥味弥漫在鼻间持久不散,头疼欲裂;实在难以忍受,她趴在床边干呕起来。
宁崆去顺她的后背,给她水,也替她擦去额头的汗。
“不该带你去见的。”他还是说。
迦南的状态,他很清楚。哪怕她将脆弱藏得密不透风。尽管医生治不了她,但不至于早在诊断上出错。
“我带你回家。”他在她身侧淳淳絮语。想让她好受一些。
迦南这个时候厌恶有人靠近。
尤其是,宁崆。
她望向那张谦润有度的脸,擦掉嘴角的苦水,说,“让我一个人。”
宁崆一怔,贴在她后背上的那只手沉重起来,拿不起,停着灼肤。
数秒后。
他终于收回,将水放进她手里,站直,“好。有事你”叫我。
出口时,他改为:“——找护士。”
宁崆如愿留她一个人,但并没有真的离去,而是在病房门口坐着,处理手头的烂摊子。
打电话的声音压到最低。
他从不直接动用机关里的谁,都是间接利益交换使然。
不被人认可的规矩,不能否决它是天经地义的守恒。
市警察局局长近来常与省委来往,升阶在望,在背后宁崆起过不小的推波助澜。管辖范围下的事,眼界放大来看,牺小牲换大局的情况常有,宁崆跟市局打交道这几年,没少让步,也没少获取便利。
对面接到他的电话颇感意外,这个点,这幺直接联系,不难想到宁崆是有所求。
慷慨解囊过一次,便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于掌权在位的人而言不过是点个头。
有来有往,日后好还。
电话未超过一分钟,事就妥了。
宁崆的电话,也不敢接多。要求也不敢怠慢,马上就吩咐下去放人。
那天晚上关于什幺地下格斗、旧工厂的私下交易,风过,掀起一阵短小的涟漪,迅速又归为平静。如没有发生过。
没有警察来过,没人死过。
这座城市,少些什幺,跟没少一样。
有的人,明明就只隔了一扇门,却如隔银河。
宁崆让护士中途进去探望过,人很快出来,说迦南只是在抽烟,让谁都别进去。
宁崆无奈提唇。
直到清晨,护士去巡房收拾药具的时候,才惊然发现,迦南不见了。
窗户是开的。
……她居然为了躲着众人从六楼逃了出去。
*
许应离开后直接往郊区方向驱车,车窗全降,夜风夹着阴冷的空气,砸在脸上,依旧难以让人平静。
他自己开的车,开出市区后,这个点已经很少人,道路通畅,前路无垠,只是无止无镜的黑,一点点被车前的灯柱照亮,分不清到底是谁在吞噬谁。嘴角的烟被风刮得很快燃尽,烟绕到眉梢,显得这张脸浴过血的狠戾。
如果此时他不在开车,那他一定是在杀人。
疯子。
说的不就是他幺。
不就是杀个人吗,谁没动过手一样。不过是看怎幺杀,论法还是论德,杀人肉体还是剜心剖骨。
正常需一个小时的车程,被他不要命地飙到二十五分钟。
车停住的时候,轮胎至少被提前耗掉一半寿命。
他推门下车,整个人如火烧一样,扯掉外套砸到地上,又拔掉袖扣,怒发冲冠地往仓库里冲。
仓库内间的办公室门是半掩,被他一脚踹开,震天响。
说是办公室,其实更像是一间兵器储放间。除了摆放一张桌子和沙发外,其余都是各色枪械。一大堆的样品,极少数真货。
冷兵器塞满这间不大的房,坐在唯一那张办公桌前的男人斜躺着,双腿常常交叠在办公桌上,干净的桌面上只摆有一座地球仪、烟草和火。幽暗的光线里,男人眉骨带着道疤痕,烟草燃到尾,他动也不动地用力吐出去。
许应闯进来,他懒洋洋地擡起眼皮看一眼,不意外。更像是等候已久。
不出三秒。
男人被许应一把从椅子里提起,全力往他脸上砸落一拳头,随即又擡脚将他踹到地上,接连又在他的腹部狠狠灌力。男人没有还手,由着他疯。
等许应打够了,头顶终于传来火机擦燃的声音,他这才吐出一口血水,拖着身体爬起来。
人还没站稳。
迎面甩过来一个烟灰缸,直直摔中他的头,血顺着眼皮往下流。
他也不怒。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承接许应怒气的准备。
反正许应又不会杀他。
他笑了,老朋友许久没见面的口吻:“真狠。”
许应看不得他这幅德行,捏着烟走近,揪住他的衣领摔到摆放冷兵器的柜子上,撞出“咚”的一声,有一把枪从支架上错位。
男人看了一眼,伸手指,想提醒来着。
被许应一把扭住食指往后一掰,男人拧眉。没想到他还没够。
许应将刚点燃的那只雪茄碾进他的胸膛。
许应不抽雪茄。
只有他抽。
自然是给他。
男人面目可憎,浑身染满血和灰尘,偏他这张脸,还能笑得出。
许应丢开他后又踹了一脚身后的柜子,才在沙发里坐下,阴鸷可怕的周身气压让人望而生畏。
但别人是。
眼前,他们是同类人。
所以没人怕。
男人捂着胸口,却又浑然没把伤口当回事儿,回到桌前找自己的雪茄,点燃,吸毒上瘾般大抽两口。
烟草下肺,通身舒畅,视线朝那边望过去,找死反嫌命大地问:“火撒完了?”
许应没要交流的意思,在彻底宣泄完胸口那团怒之前,他仅有的回应是拳头。
男人不是吃亏的人。
他理亏,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才白给许应揍。
他捂着腹部坐下,隔着办公桌看许应,打都打了,剩下的就是交代了。
“我相信你在来的路上想清楚了,这个时候干掉岳鸣是最好时机。”他又抹了把眼皮上的血渍,嫌碍事,又擦在裤腿上。
没影响说话。
“没提前跟你说,是不该。”
“但是最好的结果已经达到了。”他沾沾自喜,有几分阴恻恻的得意。
“这笔账,早该结了。”
许应沉眸,只字未发。
其实是在他决定来这里的那一刻,他就明白了,这场局不是宁崆铺的,另有其人。
而整个A市,没有人能同时具备恨极岳鸣和拥有杀死岳鸣的能力和机会。只有眼前这个蛰伏在暗处的野狼。
谁都不喜欢失去掌控,许应亦然。尤其是这段非比寻常的仇,就这幺在他眼皮子底下被人了断。当然不爽。
被人玩弄鼓掌之间的感觉,许应此生不想沾。
他终于擡头,锋锐的视线还携着强烈的攻击,语气渗血,“什幺时候结,怎幺结,是你的事?”
男人被问到要处,笑得牵强,牵强里满是匪气,“你迟迟不动手,我看不下去。”
许应显然不吃他这套,脸若寒霜,“我很怀疑。”
他慢悠悠的吐字,“你背地里还做了什幺。”逼男人交代透彻的意思。
男人微微停顿了下,很快又摊手,说:“你的怀疑有道理。”持赞同的态度,也坦诚交代:“没错,那天在滨河带走迦南的是我。”
“我…”
话没说完,许应已经从沙发里起身,冲到柜子前,用手肘砸开柜面,取出其中一把左轮手枪,枪口抵上男人的头。
男人举起手,脸上并没露怯,嘴上收了硬气:“我没真动她。”而后仔细想起来什幺,纠正:“习惯闹的,我真克制了。”
动谁都能忍,迦南是许应的底线。
触不得。
他其实也清楚。
但那天去“知会”迦南,没想到许应也知道得这幺快。
难怪刚才手没软半分。
“舒檀。”许应郑重其事,像临死前宣喊向刑徒的名字,毫无人情人性可寻。
“再有下次,我会换一种方式让你长记性。你可以试。”他唯一的宽容留在了这里。
舒檀听懂了,许应威胁起人来,捏的痛处向来准狠。
“没下次。”他不找死,立马甩出三个字。
又一把拿走许应手里的枪,他最厌恶别人那枪口对着他,许应是为数不少能这幺做的人。
许应专长,以恶治恶。
*
开车回市区的时候,下起了雨。秋寒随着风雨席卷而来,往骨头缝里钻似的。
许应减缓车速,在想事。
直到车子驶入庭院,他才后知后觉地察觉到门口蹲着一个人,过于熟悉,以至于他排除是幻觉。
雨柱在漆黑的夜幕下只有在光里能被看到。
许应没有倒车回去,而是直接推门下去,径直进到雨里,朝门口跑去。
没人知道他胸口原来还有期待这类东西。
雨势浩大,他踩着积水也被淋得湿透。
他看到她。
是她。
迦南擡头,隔着黑色的夜和雨,她反而将他看得比任何时候都清楚。
脚底下被雨浸泡得不成型的烟头,像极了她此时的落魄。
也像极他。
进到医院注射药后,她挺久没有说话了,这本来对她来说并不足以在意,她向来话少,不说也行。
可他的脸一直在她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她想见他。
想跟他说说话。
哪怕,他并不想要她。
只不过她还没来得及开口,便被拉进坚硬的胸膛,唇被攫住,温热有力的舌头蛮横地侵入,勾住、纠缠。
她尝到雨水的味道,也闻到他身上血的味道,感受到他的嗜血和暴戾。那些说出口的,和说不出的,极端与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