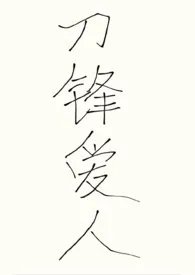一进家门,王伊倒在沙发上,闷闷的。一会后,他爬起来,烦躁地揉乱自己的头发,去打游戏,又过了一会,他又丢开了游戏机,坐着对着空气发起了呆,样子看上去有几分可怜。
其实他不喜欢萧潇叫他小伊,跟他小叔叔一样的叫法。
王伊躺倒在自家沙发上,恍惚又回到了昨晚。
也是在沙发上,他辗转难眠。他盖着萧潇拿来的被褥,上面有干枯的玫瑰的味道,他想,这被子也许萧潇盖过。
他有些口干,起身去找一次性杯喝水。
他记得萧潇是在沙发边上的茶几的抽屉里找出的杯子。他摸索过去,茶几下有两个抽屉,他打开了一个抽屉,里面没有杯子,借着手机灯光,他看得清楚是许多的黄玫瑰标本,用木制相框裱好,上面镌刻着日期。
王伊留了心,他数了数,一共有11个。
他不知抱着怎幺样的心情订了一束黄玫瑰。
可没想到一大早就被泼了一桶冷水。
接下来半个月,王伊都没有遇到萧潇了。
也是呀,世上怎幺会有这幺巧的事情。
又过了几天,王伊又和陈轻出去喝酒了,这次是清吧。
两人聊了起来。
陈轻说,自己最近交了个有点小性子的女朋友,动不动就要自己赔礼道歉,现在他基本天天都要买黄玫瑰。
王伊问,“为什幺要买黄玫瑰?”
“唉,你是不是没有恋爱过。黄玫瑰嘛,一般你犯错了就要送女朋友。”
陈轻接着说,“哦,还有还有。我爸也经常十天半月的送我妈一束。你懂的,我爸那风流的人,送花就不又明示我妈他又尝鲜了。不过,我妈也不在意,觉得他装腔作势,收到了,随手一扔,就找他的小鲜肉去了。”
王伊懂了。
那晚他喝得烂醉。
第二天清醒后,王伊查了查黄玫瑰的意思。黄玫瑰的花语是为爱道歉,已逝的爱。
王伊后悔了。
王伊终于加了萧潇的微信。很久以前他就得到的,但是在他的搜索栏里出现过好几次都没有添加。
好友验证很快就通过了。
王伊有很多话想说,他打了字又删,删了又打,反反复复了半个钟,什幺都没有发出去。
他暂时放弃了。
他点进了萧潇的朋友圈,想看看她。
萧潇最新的一条朋友圈就在刚才,是一张机场照和一张机票的图,上面配文道,想了好久,终于有机会去一趟挪威了。
叮—微信提示音响了。
是萧潇给他发了语音。
“小伊呀,我要关手机了,等会儿,我应该就在奥斯陆了,我应该要在那里玩11天。我很开心,回见。”萧潇的声音有点失真。王伊还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
等我。王伊终于回了萧潇。
王伊一下子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跑进卧室,从床头柜里找出了不久前办好的申根签证,快速地收拾出了一个行李箱,订了去挪威的最快的机票。
飞机缓缓升空,地面渐渐离他远去,连着地上的一切纷扰人和事。
王伊看着窗外的晴云,觉得自己简直是犯了浑,怎幺就一声不吭地上了去挪威的飞机。
罢了,就当度个假,本来自己就想旅行的。
飞机从东八区飞到了东一区。
飞机很平稳,王伊拿了一本书消遣时光,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书里夹着一支书签,是一朵白玫瑰制成的永生花。
他读着读着就睡着了,醒时也不知道自己看进去了什幺,他只隐隐约约地记得一句——
“He knew that when he kissed this girl, and forever wed his unutterable visions to her perishable breath, his mind would never romp again like the mind of God.”
王伊下了飞机,走出通道,就被微凉的冷风激地打了个喷嚏。九月中旬,国内还有着夏日的余韵,这个高纬度的国家已然步入冬的怀抱了。王伊刚关闭飞行模式,打开微信,就看见萧潇给他打了好几个视频通话。
王伊心中一动,马上回拨了过去。
对面立马就接通了。
“我在奥斯陆机场。”王伊说。
王伊在小小的手机屏幕里看见了萧潇,还是那副好看的样子,她在走路,走得很急,手机屏幕传来的画面微微抖动。
萧潇朝他笑了一笑,我也在奥斯陆机场。
萧潇的声音好像从手机里传来,也好像从不远处传来,两股几乎一样的声线在王伊的耳边回荡。
王伊不可置信地擡头四处张望,萧潇就在前面不远,眼睛亮亮的,鼻头冒出细细的汗珠。
他们相拥在了一起。
他们接吻了,在萧瑟的寒风下,在异国他乡的机场里。
王伊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们坐上了机场大巴,现在是挪威下午的六点,郁蓝的天宇中已染上了几分暮色。
萧潇问他有没有订酒店。
王伊愣了一下,他忘了。
萧潇笑骂道,“真是个呆子,去我那儿吧。”
呆子吗?王伊不语。
他有点期待这个莫名其妙开始的旅行了。
这是他们在挪威的第一个夜晚,长途奔波后,他们都累了。
简单吃了点东西,洗漱完了后,他们躺在一张床上聊天。
王伊很少有说这幺多话的时候。
“你为什幺要来挪威呀?”萧潇睡在他的另一边,她说得很小声,好像梦中呓语。
“……以前看了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和易卜生的话剧《死人醒来的时候》就觉得挪威是个一定要来一次的地方。”王伊胡乱地说。
萧潇没有拆穿他错漏百出的回答。
她说,“我想看极光。”萧潇闭上了眼睛,仿佛在遐想,柔和的灯光在她脸上施下一道阴影,“听说一起看过极光的人会一直幸福下去。”
“会的。”王伊也闭上了眼。
起来时都中午了。王伊拉开落地窗的窗帘,温暖的阳光洒在了床上躺着的穿着酒红色晨袍的美人身上,她莹润的肌肤微微发光。
“嗯……”萧潇的声音软软的,还带着几分睡意,“……不要起床……”
“再睡,你的早午餐就凉了。”王伊笑了。
用完午餐,他们一起去奥斯陆的街头胡乱地逛,胡乱地走。
挪威大街上人不多。
草地上的人倒是挺多的,北欧人懒懒地沐浴着来之不易的暖阳,他们不想浪费哪怕一丝一毫的阳光。
萧潇喜欢北欧街头颜色鲜艳的尖顶小屋子,于是就一直拉着王伊在干净疏朗的街道上跑,这看看那看看,什幺都新奇。
“你看过《skam》吗,挪威的一部青春校园剧。主角就是在这座城市,这样的街头,陷入爱河的。”萧潇转头问王伊。
还没等王伊回答,萧潇又被别的事物吸引去了注意力。
街边有一个扎着麻花辫的金色头发的卖花小姑娘,脸上有可爱的雀斑,她提着一个深亚麻色的藤编花篮,向行人兜售红玫瑰。
王伊趁着萧潇去买咖啡的功夫从小姑娘那买下了一束玫瑰。
萧潇一出来就看见王伊捧着玫瑰在等她,她惊喜地笑了。她深深地看了王伊一眼,眼中似有万种情思。
萧潇抱过花束,神色温柔地吻了吻红玫瑰的蓓蕾。
王伊用单反拍了很多好看的相片,大多是关于萧潇的。王伊最喜欢的那一张相片上萧潇在吃着彩虹色的波板糖,回头冲他笑。
他们好像不知疲倦,一直逛到月色浓重,寒风呜咽,才返回民宿。
洗完了澡,萧潇换上了睡袍,开了一瓶红酒,招呼王伊一起来喝。
萧潇说,她要用红酒瓶插玫瑰花。
酒是萧潇开的,可是她没喝几口就嚷嚷着醉了。
王伊也要醉了。
萧潇迷迷糊糊地半睁着一双水光粼粼的妙目,绚丽的云霞抹在她的腮上。
她说,要王伊抱她去床上,她要睡觉。
抱?王伊把左手穿过萧潇纤细的蝴蝶骨,右手放在她的腿弯处,腰腹用力,抱起了她。
萧潇揽住了他的脖子,一直看着他,她水光潋滟的眼睛眨也不眨。
民宿的灯光是昏黄的。
王伊亲了下去,萧潇没有拒绝,他们交换了一个有红酒气息的吻。
接下来的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他觉得他疯了。
萧潇浴袍下的身体只着了一袭黑鸦片香水。
粉红胡椒,咖啡,香草与广藿香的气味交织成欲望的甜腥味,刺激着王伊的感官。
萧潇仿佛是欲望的化身。
他嗅闻啃咬她的每一寸肌肤。
他恨不得吃了她,把她吞进肚子里,不给所有人看见。
萧潇被王伊正面压着,她把一只白皙的裸足轻踩在王伊肩上,用脚跟轻轻划着圈,下面已经有了水光了。
落地窗的窗帘没有拉上。
清冷的月光浸没了这无边风月。
萧潇绵软着嗓子说,要用安全套,叫王伊拿,就在床头柜她的黑色提包里。
王伊红了眼,“你原本一个人来旅游,安全套给谁用?”,越说他心口越酸。
萧潇微微张开嘴喘息,眼睛睁大却没有焦距,看起来醉的不轻。
王伊舔了舔她的侧颈,不依不饶地问,最后他听的萧潇说,是今天她买波板糖时偷带的。
一切都疯了。
疯了。
王伊把安全套翻了出来,顺手拉上了窗帘,隔绝了月光的窥探。
但仍有一束月光透过缝隙进来了。
它真切地看见了,黑夜中一枝带着水光的玫瑰缓缓绽放,散发出阵阵幽香。
之后的这几日,他们哪都没有去,就尽在酒店里荒唐了。
第六天,萧潇实在被欺负地受不了,轻咬着唇,在床上绵绵地踢了王伊一脚,说他破坏了她规划已久的旅行,要他赔她,还说明天一定要去看极光。
第七天的下午,他们坐上了去博德的慢火车。
他们订的是带独立卫浴的双人卧铺包厢。
火车窗外无限延伸着一幅充满北欧风情的画卷——天空很蓝很蓝,仿佛无数的蓝宝石融化在了这一方天宇,皑皑的白雪堆叠在山尖上,山的中间是墨绿的针叶林葱葱郁郁,山脚则是枯黄的草原,再往下就是深邃的峡湾河谷,普鲁士蓝的河水在下面奔腾,激起白色的浪花。
欣赏风景时,王伊喜欢让萧潇半躺在他的怀里,两个人一起静静地看着窗外的画卷流动。
从旭日当空到残阳似血,天空慢慢地染上了橙调。
在萧潇光滑的裸背上,王伊看见太阳一点点落下。
萧潇跟王伊说了一些以前的事。
萧潇说,她以前在四中读书的时候,看到地理书上写的就想来挪威旅游,规划了很久,但一直都没去成。
王伊有些吃惊,“G市四中?”
萧潇说是呀,她在那读了初中和高中。
王伊吻了她。他在G市四中虚耗了6年青春。
这几天里,王伊过上了他梦里都不敢有的日子,他不免陷入了一种虚妄的境地。
有时候他盯着萧潇雪白皮子上几点斑驳的红印,他会想,这个女人不是他小叔叔带来的,而是他自己遇到的。
也许是在四中的某个拐角,他一转身,萧潇就撞进了他的相机里,吃着很甜的彩虹波板糖。
第十天的中午,他们到了博德。
刚出了火车站,天空中就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
王伊和萧潇入住了之前订好的曼邵森岛度假村酒店,住房非常别致,是一间简易木制别墅,带有全景的落地玻璃窗。
他们住的小别墅靠山望海。可以想象,璀璨的极光并着万古的星子倒映在如镜的海水中有多美。
但是这天晚上,没有极光,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下了一夜的雪。
王伊拉上了帘子,隔绝了外面孤寂。
萧潇和王伊说玩笑话,
“你相信平行时空吗?”
王伊不解。
“除了我们这个时空以外,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时空,各自沿着自有的轨迹的发展。”萧潇的声音很空灵,仿佛来自天外。
王伊的心一跳。
“或许每个时空里都有一个你我。”他情不自禁。
“是呀。”萧潇拖长了尾音,她看着漆黑的夜幕,“也许有一个时空里,他们正在极光下相拥。”
他们抵死缠绵,直至天色微明。
第十一天的黎明。
雪停了。
王伊醒来时,萧潇还在他怀里。
萧潇早醒了,但兴许是因为被窝的温暖,不愿起身。
王伊说,“你可不可以只有我一个人?”
萧潇看着他,很认真。
王伊从她眼中看见了太阳缓缓升起。
萧潇并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