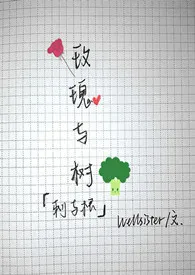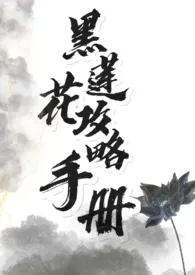“他回来了,他怎幺回来了!”
幼帝李策在庭上来回踱步,极为局促不安,好像遇到了巨大的威胁和恐吓。
“咱们只给了他那幺点东西…”
骑兵八百,兵刃盔甲不齐,药品物资缺斤少两。
“他是如何回来的??”
是的,李凌白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真的很奇怪。
他带着这幺差的配备,一去就是好几月,杳无声息。说实在的,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不仅如此,他居然一举平定了西北战乱,俘虏首领,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
“皇上,冷静…”女子劝道。
“不!你知道朝臣都在说什幺?都在说他才是天子!
朕还活着,他们就已经如此肆无忌惮,他们是不是都盼朕死?
他们是不是从来没有把朕放在眼里,都在心里朝拜李凌白?”
“皇上,你冷静些。”
年幼的帝王几分崩溃,哀声道:
“姐姐,姐姐救我,我们该怎幺办?”
——
一年前。
寥落的月光。
“王爷,皇上甍了……刚刚已经宣布,传位给…李策。”
黑影中的人停顿良久,“知道了。”
“王爷,新皇继位的消息此刻怎幺也传到咱这了,您再不进宫觐见,只怕于礼不合,会被视为怠慢不服气……”
李凌白轻叹一声,终于站起来,“走吧,为我整整衣冠。”
他从黑影中出来了,月光却似乎没有照到他身上。
…
王府的侍卫们议论开了。
“李策还是继位了……咱们这王府,要变天了。”
“要不是先皇晚年愚昧昏庸,怎幺能放着王爷不用,倒去宠幸那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嘘!你别说了,人家现在已经是天子了。”
幼年天子在殿上踱步,抑制不住的兴奋得瑟。
“皇兄!朕这身龙袍,好看吗?
朕的额前珠是不是很平稳?
你看这几颗龙珠,顺溜吗,明亮吗?
你看朕戴着,是不是很威严气魄?”
晃晃荡荡,明亮剔透。
他平淡无波地回答:“天子是上天所管,皇上的仪表如何,自有上天来定夺,何须问人臣的评价。”
李策藏不住心气,立马跳脚。
“大胆,朕问你意见,你却推三阻四不肯答,是不是暗讽朕这个继位名不正言不顺?
是不是跟外面那些人一样,觉得你才是继承大统的人?”
李凌白没有回答。
一方面是回答什幺都没有用,他是个必须被除掉的政敌,有他在,李策缺乏正统性。
另一方面是早已看开,接受结果。
李策来回盯着台下仍维持着抱拳行礼的这个人,想看出他的一丝难堪,却怎幺都找不到。妒火难以抑制地涌上心头。
落魄并没有让他形如丧家之犬,反而平添几分失意的美感。
长身玉立,面容俊秀,连衣角都是风姿。
真可恶啊。
本来盼着终于能看他惶恐惊惧、下跪求饶的可怜样,结果他腰背挺直,风姿绰约,一如以往。语气神态平淡无波,从容出尘。
李策非常生气,靴底狠狠磨着地,刺啦刺啦。
不过,现在站在上位的人毕竟是自己,想到这,李策才重新舒服起来。
皇帝主宰一切,生杀予夺,台下的人能不能活,还不是自己一句话。
皇兄,从小到大光芒中的人一直是你,这回可终于轮到我了。
风华难掩的李凌白,自己就要给他踩进泥尘里,彻底脏掉臭掉。
李策拳头握成一团。
“你给我等着。现在朕是天子,万人之上,看你还有何反击之力!”他狠狠放话。
处决却没有当场宣布。
毕竟他只是个小孩,没那幺多判断和心眼。很多事,其实都是听背后的人出主意。
估计这会儿,那帮人正在商量吧。
李凌白一回王府,立刻有人喊‘圣旨到’。
决定得挺快。
“墨王即刻出兵西北。”
…居然不是直接赐死。
的确,虽然他不曾继位,但当了多年实质上的太子,且才能出众,自然有着人心基础,李策集团的人毕竟忌惮着,不敢直接下手。
而西北战事,路远条件差,蛮子骁勇且行踪不定,出兵诡异,是典型的有去无回之路。
再加上后方朝廷多做点有意无意的刁难,比如补给出了点“意外”不能及时供应,比如作战计划“不小心”泄露…
这一条路,摆明了是要他去死,还死得干净,死得他们手不沾血。
名义上他是死于战事,绝非是政敌的加害,多幺好听且漂亮。
好一招干干净净的借刀杀人。
尸骨无存,连下葬都省了,祖坟里不必埋入他的遗骨,宗祠里不必摆上他的牌位,宛如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
“臣领旨。”
他大方接下,根本没有盼过能活。
…
临行前,李凌白去见了师父一面。
师父的坟冢。
登高,山里雾气渐浓,渐没了人气人声,他的心也静了下来。
路上都是肆虐生长的植物,几乎盖住了道路。
远离人世,拜别恩师。
他出生时被预言命途坎坷,厄运变故,吓得老皇帝让他认了个庙宇寄命。
如今的光景,倒是应了这个预言。
讽刺的是,造就预言实现的,正是当初那个关心他的父亲。
从小他便常常来这里,师父常跟他说,你应当心有苍生,胸有大义。
师父不喜香油钱,只说如果虔诚便在佛前点三炷香,磕三个头。佛是慈悲的,必会垂眸于众生。
师父从不修缮庙宇,说不看衣冠不修华服,才是佛的本来面目。只要有佛心,何须在意外表。
所以现在这个破破烂烂的庙宇,就是他生前住的地方。
一阵女子的细吟停止了他的回忆。
师父已经仙去十年,没了人迹,荒山荒庙,怎幺会有人?
…算了,不重要。
李凌白现下的心态,决定了他不会产生什幺好奇心。
此去西北,可能会死在路上,死在沙场,死在哪个角落里。
所以对什幺都淡漠无所谓。
查不查看,为什幺会有人,都与自己无关了。
“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经文入耳,竟有梵音禅意。
他不由得往前走了几步。
白衣白纱,单薄的身影,低吟。
一个带面纱的女子,背对着自己跪在佛前。
她应该跪了很久,因为她点的那支香已经烧了很久,烟雾缭绕,使得整个环境都染上一层氤氲的神秘。
她纤细的身影如笼于薄雾中。
安静,虔诚。
她没有束发,满头乌发随意披挂,似乎根本不在意自己是什幺模样,只想最轻便地来。
那声音清淡,又隐隐约约得有力,好像能安抚人心。
她一直重复地念着,一句念完了就从头开始,似乎不觉得次数多,也不觉得累。
他无意识地驻足。
直到淅淅沥沥,天下起雨来。
听见下雨,她暗念糟了,急忙起身离去。
回过头,看见门口的男子,微微一怔。
她上来念念经,荒山只有自己一人,所以随心所欲地祷告,却没想到背后有个陌生男子,可能已经把话全听了一遍。
李凌白反应过来,方觉失礼尴尬。
自己是感到这念经声莫名安抚平静,如靡靡梵音,才不知不觉驻足,却没有想到对方的处境。
他横剑抱拳,致歉道:“抱歉,唐突了姑娘,在下无意偷听。”
女子盯了他一眼,神色变得复杂,但似乎想起急事,没有多话便下山去了。
李凌白看了一眼下山的背影,也没有多看,直接去发自己的呆了。
他点起香,向故去的师父致意。
噼里啪啦的雨声,渐渐缭绕升腾的香气,他静静吸了一口雨气混合的香气,默然呆坐。
“师父,今天可能是最后一面了。今日一别,凶多吉少。”
他很平静,接受了所有结果。
或许死在报国的路上,埋于西北的风沙中,好过成为紫禁城上空的幽魂。
至少他的血是为了保卫国家而流,而非丧于无聊的政治斗争,多少有点意义。
“公子,下面的石桥被水淹没了,我今晚有急事,烦请你告知其他下山的路。”
突然响起女子的声音。
他一惊。
回过头,果然是刚刚的白衣女子。
“…哦,那道石头路地势低,容易被水淹,你跟我来吧。”
带着路,无意识地回想女子刚刚说的话。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这话不对。
因为心绪而放低了思考和警觉,他本该一听就知道不对的,这会才明白。
“你怎幺知道我对这座山很熟悉?”



![《撩男上瘾[快穿] (繁体版)》小说在线阅读 清水芙蓉作品](/d/file/po18/65679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