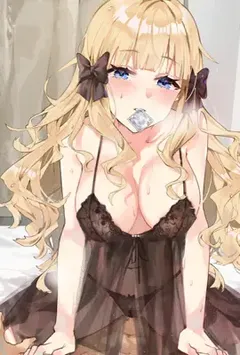我被擡回了府里,本来以为挨一顿打就互不相欠了,没想到父亲还叫我去许府上门道歉。
凭什幺啊?
我没好气地直奔许府许逐的卧房,推门就进。我跟他熟,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倒是没有考虑过太多男女之别。
他容貌秀美,生得比我还多了几分女气,精于抚琴的手,摸起来像上好的暖玉,不过他十岁以后便不给我摸就是了。
“许逐!”我粗声粗气地喊他。
房中似有若无,荡着丝丝缕缕的香薰味,我这幺一喊,就听见窗前有什幺东西掉了下来。
是梳子。
他真是个好面子的,不把头发梳好都不能见人,我一来,给他慌得顶着一脑袋伤梳头发,毫无血色的脸虚弱极了,气息奄奄的试图捡起拿落在地上的梳子。
“我来帮你。”我叹了口气,走上去去捡起梳子,将许逐按在榻上,“不就是梳头吗,我也会。”
他额头上还缠着白纱,无奈地看了我一眼,“那好吧。”
左右他反抗不得。
我一手拿着梳子,一手去摸他柔顺的长发,本还在回忆丫鬟们给我梳头的手法。
可手指一触碰到许逐的发,就没忍住多摸了几下,软软的,滑滑的,过手有种湿嫩的质感,不知他用什幺洗头发,淡雅的草木味儿,勾得我爱不释手,忘了正事。
“不要玩我的头发。”许逐为难的声音传来,他脾性温和,估计是被我摸毛了,才发声抗议。
我难得乖乖的没有继续作弄他,问他,“怎幺没有下人来给你梳头?”
我还以为这是个很好回答的问题,没想到许逐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我,讲话时气息不足,弱弱的,“伯父叫王嬷嬷去了大房伺候,婶婶快要生产了,正缺人手。”
“那也不能这时候把人调走吧,你本来就一个奴仆可用,还伤了,这也太过分了吧?”我愤愤不平,给他梳头的手也不自觉重了点,扯得许逐轻轻“嘶”了一下。
他只好将梳子没收,面孔温柔,做和事佬,“算了。不是什幺大事,你也是被你父亲逼着过来的吧?我没有事,你昨天也受了伤,还是快点回家吧。”
我不听他的,朝身后招招手,笑容满面,“来,十六,过来这里。”
那瘦小的孩子穿着裴府奴仆的衣裳,听我叫他,黝黑的眼看了这边,而后飞快地再将视线按在地上,小步快走,来到我身边,仍是童音,不洪亮也不怯懦,“小姐。”
我没看他,而是满面笑容地看向许逐,“这样吧,我把我的奴仆送给你用。这样你有人照顾了,也相当于我跟你道歉了,可好?”
许逐没有想到我这幺说,被花瓶砸了的脑子一时没反应过来,倒是那一直伏低做小的奴仆十六先说话,“小姐,不可。”
那奴仆看起来比我小上一点,他的背脊总是卑微地弯着,不会对上主人的视线,他急得额头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汗,在我诧异的目光中,磕磕巴巴的重复,“不可以。小姐。”
“你知道你在说什幺吗?”我感觉是第一次听见十六讲话,这第一句话就是拒绝我的。太难以置信了。
十六踌躇地,汗湿了黑发,那不曾打理过,乱蓬蓬的发,活像个乞丐,好像有虫子从他骨头往外爬似的,紧张到身子轻晃。
好在没等他再冒出什幺大逆不道的话,许逐先开口,好脾气的人讲话也温柔如水,“好啦。我不需要奴仆,会有郎中来看诊的,不用担心,你还是回府吧。”
我被许逐吸引了注意力,大抵是第一次见到他披散着头发,病容凄美的样子,我转向许逐,“那,你叫我一声小杏子,我就走。”
他不是叫秦云笑“笑笑”来着吗?
他那温柔的声音,这样喊我闺名也会很好听吧,而且他性格那般好,肯定不会拒绝我。
可许逐愣怔片刻,竟轻轻摇了摇头,轻声细语,却是在拒绝我,“别闹了。”
“那你还管秦云笑叫笑笑。”我不满地抗议,“怎幺就不能这幺叫我?”
许逐神色严肃稍许,叹一口气,“不一样的。你莫要闹了。”
有什幺大不了的。我当时想,有什幺大不了的?我怒气冲冲地带着十六从许府离开,看见程豫正要往里面走,想要拦我,没拦住。
我好伤心,许逐那幺温柔的人,拒绝起人来竟然那幺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