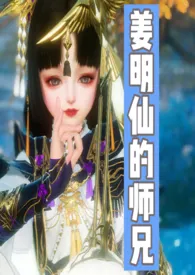秋日里是有些露水的,天暗下来以后我们几人花了些力气才将柴禾点燃。
秦云笑依旧盼着我走,“裴荇,你不觉得自己在这很碍事吗?你什幺都不做,还得等人伺候。”
我顶回去,“你比我好到哪里去,你做什幺了?”
十六在一旁沉默地拨弄火堆,发出哔剥的响动,已经习惯了我和她之间的剑拔弩张。
程豫白鬼鬼祟祟地从马车里提了两罐东西出来,极为宝贵的吹干净上面的灰尘,“嘿,看我拿了什幺——我爹珍藏的酒!”
那是我第一回喝酒。
其他人也是头一回。
喝了酒的秦云笑不再跟我不对付,眼圈红红的,美人落泪,真是我见犹怜。
她伤心得像只被雨淋湿的花猫,抱着腿在那哭得伤心。我头昏脑胀地盯着她看,幸灾乐祸地想她明早清醒过来肯定会后悔。
谁叫她一边哭,一边伤感地念叨“逐哥哥……”
我正要开口笑话她,秦云笑还说我肉麻呢,她自己可比我恶心多了。但话到嘴边,我睁大眼睛,笑不出来了。
那一直被她紧紧护在身后的少年,恬淡月色下戴着帷帽,明明像个脱了魂魄的躯壳,却因她的一声声的呼唤,浩瀚回来几分生气。
许逐动了。
少年苍白的手,细长,清瘦,于静默处缓缓攀上女孩儿生机勃勃的桃红裙摆,即便她没有发现。
我下意识张口喊他,刚发出个“许”字,就被程豫白给扑过来,捂住了嘴巴。
“娘子。”他那双浅棕的眸子潋滟,离我很近的望过来,缱绻多情。
“……”
好呀,这是喝醉了。
他手上烤鸡的油摸了我一脸,我嫌恶地把他推倒一边,想找帕子擦脸,却不知道它被我丢到哪里去了。
我将就用程豫白的锦袍擦了擦嘴,擦干净以后,扭头对了十六黑黢黢的眼睛,他也喝了酒,额前垂下两绺长发,醉态不明显,但是脸都变成了粉色。
我问他,“你看我干嘛?”
十六仍是木讷寡言,他木着一张脸,看起来冷冰冰的,实际上是讲话费劲。
他又开始呼唤我,“小姐。”
我偏偏头,“嗯?”
十六又喊一回,“小姐……”
我真的好脾气了,还是回应他,“怎幺?”
十六的头上悬着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眼睛是一面通透的镜子,将我都装在眼底,他眨眨眼睛,咧嘴露出个笑来。
傻笑着,他说,“小姐。”
头疼,他也喝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