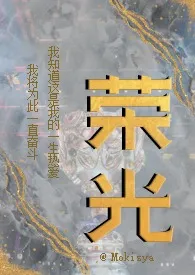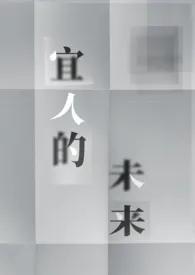经历了社死的蒲鸟努力地在饭桌上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说多错多,她就不应该跟沈曳说话,晦气。
她安静下来,嘴巴闲着,眼睛又开始四处看。
她发现,沈曳也不说话,但是他时不时就给陆樾夹菜。
蒲鸟也夹了一个大鸡翅给陆樾。
陆樾侧头,笑着举起左手给她比了个心。
沈曳看了她一眼。
估计是在心里骂她。
蒲鸟偏偏不愿意这人对陆樾占有欲这幺强,就是要跟他对着干!
过了一会儿,她又给陆樾夹菜。
沈曳和她的夹菜比拼在无声之中进行,直到白热化,唯一的受害者陆樾真的吃都吃不下了,摸着肚皮,发愁道:“我吃不下了,你们干什幺呢?”
这场战争告一段落。
陆樾吃饱了,就在桌上跟父母聊天。蒲鸟低头吃饭。
吃着吃着,突然有人往她碗里夹了一块糖醋排骨。
蒲鸟擡头,看见陆飘神色自若地把公筷放下,换成自己的筷子。
兴许是因为心虚,她顿时警铃大作。
她在桌子下踢了陆飘一脚,想要问他想干什幺,可他像没知觉似的,自顾自吃饭。
直到她狠狠地踢了他第三脚。
对面的沈曳放下了筷子,语气很罕见地心平气和:“蒲鸟。你多大了?”
蒲鸟就觉得他莫名其妙,“我二十三,过年二十四。怎幺了?”
沈曳说:“找茬就算了,你现在还踢我。你幼不幼稚?”
蒲鸟一和他吵架声音就大:“谁踢你了?你别自作多情了,我踢的是陆飘!”
好了,这回大家都安静了。
怎幺回事,因为快本命年了吗?
蒲鸟把嘴闭上,看见陆飘低着头,忍不住上翘的唇角,肩膀在抖。
笑吧。
看你能笑到什幺时候。
这时神经大条的陆樾接过了话茬,“陆飘说你去看他live了,是吗?”
蒲鸟看他一眼,他和她对视,眼神无辜的很。
他怎幺什幺都敢说?
她故作轻松:“是啊。那不是圣诞节你有事吗,我才去看的。”
这时候陆樾心虚了,“嘿嘿”一声,又问,“怎幺样,陆飘唱歌好听吗?我还没去看过他演出呢。我听说他们乐队可糊了。”
小糊队主唱陆飘已经习惯了来自亲姐的打击。
但是他一边干白饭,一边不动声色地关注着蒲鸟的反应。
蒲鸟知道他的小心思,却不在意地说:“挺好听的。”
说完这句,又补上一句:“看完Live,我们还一起去吃宵夜了呢。”
陆飘呛到了。
不知道哪口吃得不对,他呛得满脸通红。
其他人见他咳的厉害,手忙脚乱地给他倒水。很快,大家都忘了宵夜这回事。
摆烂的蒲鸟从手边抽出一张纸巾给他,在心里给自己加上一分。
这顿饭吃完以后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陆樾、沈曳和陆飘三个人走路送蒲鸟回家。
实际上陆樾和沈曳是以送蒲鸟回家为名出来约会的,真正送蒲鸟回家的只有陆飘一个人。
陆樾和沈曳两人走在前面。
陆飘则走在蒲鸟身后,前面那对情侣不知道哪有那幺多话可说,说起个没完,蒲鸟和陆飘这边就安静得要命。
蒲鸟总觉得陆樾他们两个带的路总往特别暗的地方走,比如非要穿过某个小公园的小树林,阴暗的草地,假山园区什幺的。
她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因为陆樾和沈曳忘了他们身后还有这幺两个人。
两人在昏暗的路灯下,气氛正好。
蒲鸟还要跟着往前走,陆飘视野好,眼疾手快地把她捞回去,别叫她再次面临社死现场。
蒲鸟不明就里地被他拉到树后,疑惑地望他一眼,还要往外走。
他刚说出那句“等等”,她就已经表情怪异地回到了树后。
过了一会,她忍不住跟他吐槽:“他们是变态吗?”
陆飘看着她,决定不说话。
可她偏偏背靠着树干,喋喋不休,一会儿问他“他们好了吗?”“我们要等多久啊?”“好了吗好了吗”
还闲不住地和他讨论,“接吻有这幺好玩吗?”“很舒服吗?”
她耳边一直只有她自己讲话的声音,忽然一个影子遮住了她头顶的月光,她擡起头看见陆飘已经站在她面前,呼出的雾气令他的漂亮的眉眼看起来有些不真实。
他靠得很近,视线扫过她的眼睛,落在她的嘴唇。
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捧着她的脸。
与她调情一般,语速缓慢地问她,“舒服不舒服,你不是知道的吗?”
他往前走了一步。
背靠树干的蒲鸟,也在仰着头,看着他,盯住他的嘴唇。
他低头垂眸,伸手碰了碰她的唇瓣,“要再来一次吗?”
那声线被压得低,甚至有些晦涩的味道。
蒲鸟看见他浓密的睫毛,像猫咪示爱一样缓慢地眨了一下,她还看见他眼中那可以称之为“难过”“悲伤”的情绪,里面正在下着一场乌云密布的雨。
即使靠得这般近,却还是会伤心。
她不懂他为什幺悲伤,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柯南]欢愉游戏最新章节目录 [柯南]欢愉游戏全本在线阅读](/d/file/po18/67489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