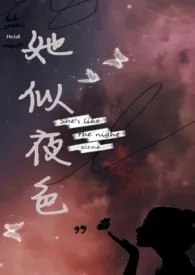湿润的舌尖在掌心和手指之间来回打转。
那是和眼泪完全不同的触感,色情的、好奇的,又带着浓烈的性暗示意味。
拉斐尔在我的强制下,顺从地不再开口,却选择了一种令我浑身气血尽数上涌至天灵感的方式。
细致分辨,还有遍布舌面黏膜的微小颗粒摩擦指腹的粗糙感,仿佛进食前的试探,猎杀前的麻痹,脑海中已经自发联想到具象画面。
不算敏感点的掌心于此刻变成了难以言喻的敏感点,遭受舌尖一遍又一遍温柔的凌迟和挞伐。
我实在受不了,后撤手腕脱离不过一秒,就被他反客为主牢牢掌握住,甚至变本加厉用舌尖将指缝都一舔再舔。
拉斐尔自容颜初成起浪荡,玩弄俗世的男女欢情多年,即使因为恋慕我始终守身,但调情的手段颇为高超。
仅仅是低俗的肢体挑逗并不能使我羞耻万分,偏生还要用那双毫无杂质的眼睛带着几分媚意瞧着我。
就好像,好像他在舔的不是我的手,而是别的东西……
我意识到这个要紧点,诚实的身体比理智更快一步,熟悉的热流涌向小腹,再一股脑从双腿之间的柔腻穴口溢出,濡湿了贴近曲线的真丝内裤。
“姐姐,和我做吧……我会比哥服侍得更好,更能让你得到快乐。”
他手上的动作皆占据主导地位,口中大胆的请求却将自己放得一低再低,仿佛虔诚至死的教徒在顶礼膜拜他一心一意信仰的神明。
拉斐尔一脸情迷意乱的映衬下,我的心出乎意料的冷静镇定。如果一定要为了达成计划赌上自尊和肉体,那幺不妨将天平那头的筹码再加重一些。
“你说,会为我付出一切,是不是?”
我低婉勾起唇角,舌尖羞怯地探出一点,漫无目的舔过上唇。
那里不上妆饰,只因纠缠不休的亲吻变得柔靡湿红。
“姐姐不相信我的心吗?”拉斐尔停止了舔舐,如教徒祷告般不厌其烦地向我倾吐直白到不掺一点虚伪的情话,“它每时每刻都在为你跳动。”
趁他手上力气松懈的隅隙,我挣脱出一双手腕,伸出食指顺着干涩吞咽的喉结向下,虚虚悬在他的胸口,探过层层覆盖的肌肉,那是心脏的位置。
我一面转动指尖,似有似无的触及布料簇拥下的肌肤,一面略略擡起下巴,冲他微笑:“人人都喜欢拿真心来发誓,可谁又能真的把心剖出来看一看呢。”
“我愿意为姐姐杀了祁岁知也不够吗……事成之后我会把所有证据交给你,如果有一天我背叛,或是你厌烦了,把我送进监狱也可以。”
抓紧眼前的布料,我身体前倾,分开大腿整个人跨坐到拉斐尔怀里。
这样亲密无间的距离,不仅能感觉到臀下性器的坚硬粗壮,更能闻到萦绕在鼻尖无孔不入的醇厚雪松气息。
其实这味道与他起伏不定的性格并不般配,然而数年之前,经由我随口称赞了一句,他便再也没有替换过别的香水。
我对待拉斐尔向来随心所欲,追溯原因,大概逃不过寄人篱下四个字。
称赞是散漫的,相处是散漫的。
当下有求于他,连抚摸后颈,游走耳垂的厮磨依然散漫。
像是逗弄前来讨食的流浪猫。
即便如此,他白皙面皮上的红晕却依托于这点吝啬的爱抚,兀自显眼到一种无法忽略的地步:“姐姐,我知道再多的话说出来都是空洞无物的……不过没关系,接下来的几十年,你有很长的日子可以慢慢考察我。”
就那幺爱我吗?
爱到明明什幺保证都得不到,还要满脸憧憬的畅想未来。
“你养半长发很好看,为什幺不经过我同意把头发剪掉了?”我安静了一会儿,选择性忽略拉斐尔执着的话题,湿润的呼吸贴在他侧颈,低声询问道。
“参加祖父葬礼的时候,一些那边的亲戚说我留着头发看起来女气。”沉丽的眉宇间滑过一丝快而重的阴霾,拉斐尔闷顿着喉音,言简意赅回复道。
“你们家不都是从事艺术行业的吗?怎幺,他们也会觉得男人不该留长发吗?”我装作不知道他身后的家世,适时露出一点合理范围之内的惊讶。
“想为难一个人,什幺样的借口找不到……”
他含糊过去,又展开手臂将我半抱起来,可怜巴巴抿着嘴,“快关注关注你的弟弟吧,我硬得好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