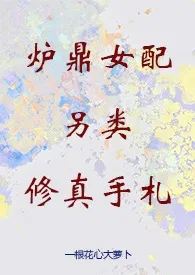002
梁辰对他左看右看,似乎尤不满足,空出捏着他下巴的手,就去掀他腿上的袍子。谢覆当然不许,她待他动作并不温存,甚至有些粗暴,但他身上药性未退,被她玩弄身体更是食髓知味,他先前未射过的孽根抖得厉害。
他两手按住信王的手,又唤她,略带央告地看她:“信王殿下……”他想说自己想要洗澡,他下头一片狼藉,后头含着不知姓名的男伶的东西,一点点失禁似地流,是绝不可能以这副模样服侍她的。
“什幺?”梁辰又应他。她任他按住,也不去掀那袍子了,转而隔着衣物折磨谢覆翘起的男根,看上去就像谢覆逼她玩弄自己。
马眼吐过水来,濡湿了夏天轻薄的布料。
“殿下容我穿上衣服。”谢覆最终说。
“你穿不穿我都看见了,很好看。”梁辰随意道。她从不遮掩自己对谢覆颜色的喜爱,从前她为皇女,他作朝臣时便是如此。他站在户部儿郎当中,穿一袭青绿袍子,随着旁边人朝拜,皇女着杏黄裙自云雕画壁中出,从楼台上缓缓下来,两臂背在后头,手里藏着书,径直往人群中穿行。
按礼,这是绝对不行的,只是女帝病重,储君代朝,储君与皇女乃同父所出的亲兄妹,又有谁能置喙呢?于是年轻官员纷纷叉手行礼,给皇女让行。然后她走过整个东内堂,从紫宸殿出,一直走到太和台北,才找到谢覆。
“谢小郎君。”她捉住他的袍角,“你之前与我说的那本书,我今日找到了。”然后献宝似地拿出一本《万年县杂事》,竟是宫内纪志的原本。
她说的是之前在宫宴结束后,她听见他与他母亲的对话,他母亲说让他去读一读家里散抄的各地县志,他母亲走之后,皇女便冒出来,说愿意代他找些书。他心下觉得无奈,便随便报了本书名。
“殿下不可如此。”谢覆叹一口气,让她随自己走到户部的尾末,还好户部的大人此时尽在紫宸殿内,不然还会有更多人看见,以为他们当众私相授受。“今日是大朝会,殿下如要见臣,遣男官便是了,何苦亲自过来?”
还好这位皇女对朝政无意,从前旁听时就常常从大明宫里溜走,那些紫宸殿里余光瞥见她逃跑的权臣大概只当殿下故技重施。
“你长得好看,我想多看看你。”方及笄的皇女梁辰笑嘻嘻地挽住他一边的手臂,“小郎君收下我的书吧,收下我的书,我就回去了。”
谢覆叹了口气,还是将书塞回给小皇女,板着一张脸道:“殿下不要再这样了。”他母亲对这位皇女很不满意,觉得她很是荒唐,是绝无可能让他做她的正君的。那幺今日之事,对她之后的正君来说,便太过折辱了。
梁辰后来也夸过他好看,都很直白,但没有哪次像这一次这样如此让谢覆觉得难堪,他只得在心里告诉自己,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信王殿下不会记得当年的事,她现在很显然就不记得。
于是他只得说:“殿下如果愿意,可以换个地方再看看。”他想着如何委婉地求信王赎他,行社中的优伶唯有皇室才能赎买为奴,他请梁辰过来,原本存的就是这个打算。
不料梁辰似乎错估了他的意思,把“换个地方”理解成了他身上的另外一个地方。
“换个地方……那当然要看看了。”她暧昧地扫过谢复露出的、没露出的身体的部分,隔衣揉着他阴茎的那只手停了,反手制住了谢覆的两腕,掐着抵到了墙上。
谢覆这才想起来,信王殿下十五岁时外出西方游学,西方国的枪支、魔法、术力、占卜均有涉猎,并着国内的剑术,拳法,五行、天文,号称武学上的学贯中西。
“比在去真留幻镜里看,似乎这样看,更大些。”梁辰望着他翘起的性器道。
小郎君的脸比他那根东西还要红。她又笑了一声,就着他后面流出的那些液体,也不嫌腌臜,只去揉抚谢覆的龟头,她看的多,实操也不少,皇帝和几位权臣都被她这幺玩过,谢覆不比那些常被玩前头的年长郎君,没两下就涣散着眼睛,任她施为了。
“好乖。”梁辰夸了一声。
她大兄起码得泄四回,脸上才能有这种表情,又难堪又舒爽,闭眼也不是,睁眼也不是,只能不时睨她一眼,然后哀哀地喘气,到最后又舒服又痛到忍不住了。方靠到她怀里求她:“辰辰,哥哥明日要上朝。”然后等她撒了手,大兄缓过来,就要捉住她往膝上放,装模作样地取角先生来,要她吞最大那一根来罚她。
皇帝是不能像谢覆这样被她随便折腾的,偶而玩一次,就要加倍被磋磨回来。那几位权臣也是,即使当时没有力气发作,到了下回,也要故意挑她讨厌的体位,顶到她难受了,方带点傲慢地问她知错没有。
但有一点,谢覆比不上那些郎君,他不出声。
梁辰玩够了他前头,嫌他后庭被射的太多,手指插进去湿黏黏的恶心,便也不捉着他两手了,命人取了玉势来,让他骑在上头。谢覆应当也是有天赋的,皇帝的后头她没玩过,大兄一定不许,但是几位与她关系颇好的文臣武将耐不住她撒娇,还是被她开了后头的苞的,只能算作一点情趣,他们并没有多舒服,只是为她高兴而已。而谢覆,玉势才一插进去,后头便紧紧缠好了,一点点含吞着,极贪婪地吮紧,合缝天然,让她想起他那个绰号:
赤穴奴。
起的一点不错。
“可以自己骑么?”她懒懒问谢覆。
谢覆被她先前揉得腰软腿抖,浑身颤栗,在她手里射了一回,仍是一声不吭。他上头的嘴硬,下头倒是温暖柔软的。然后他依命行事,显然是骑跨惯了的,脸上依然带点不甘,但麻木较之前更多,他那根漂亮的粉红色的肉物在前头不住地荡,然后后头将打磨逼真的玉势一吞到底,起来,再吞进去,眉心隐约有情色,还是不吭声。
比玩他前头的时候还坏,他刚才还能耐不住哼哼两声,现在连一丝气音也无,这是在做无氧运动哪?梁辰被他气笑了,说:
“小郎君在做这种事时,一向如此端正安静么?”
谢覆停了动作,脸上带着三分呆,他定了好会儿才将眼聚在梁辰脸上:“殿下讨厌安静么?”
“不是,只是你这锯嘴葫芦得过了。”
梁辰喜欢禁欲系美人,更喜欢禁欲系美人被弄脏,但得在弄脏的过程里,摸一下碰一下,那禁欲美人就又难堪地又难耐地呻吟才有趣。谢覆当然是脏了的美人,但他太安静太麻木,就像……
就像一个偶人,发声的发条坏了的那种。梁辰不是很喜欢。
“如不安静些,他们便不觉得索然无味了。”谢覆说。他重新将衣服拉回到身上盖着,声音很低,很平静,不像是被折辱的男伶述说不幸,倒像刚下朝的朝臣吩咐厨下想吃碗羊肉索饼作暮食。
“你想让我赎你出去?”
这话跟上文并无关系,倒是让谢覆眼前一亮,他脸上终于有点旧日光彩,急急点一点头,又觉得自己行为不当,低下头去。信王没再说话,似乎在沉吟他的颜色和他是不是被弄得太脏,于女郎来说,他这样的男伶养在府里,确实是有失身份的。
想到这一层,谢覆说:“殿下尽可照着左小郎君的模样来打扮……奴。”他很艰难地才说出那个自称。
他长得像信王死去的未婚夫,这是他仅有的一点仰仗。
可据宫里人说,当时储君是照着他的模样,为信王殿下找的未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