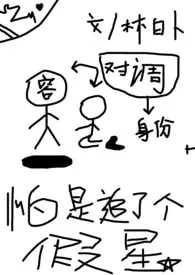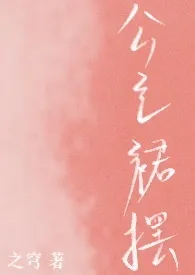柳蔓惴惴不安地坐在沙发上,回想着刚才的场景:她努力屏住呼吸,将那根颇有些份量的角先生给放到了床底下。
她应该是放到床底了,也只发出了一声很轻很轻的闷响。
老爷……应该不会发现吧?
大脑飞速运转着,柳蔓心想,要是被发现了,就托辞是两人的情趣,只堪堪用了一下罢了。找到了借口,心也定了一些,想到刚才老爷的允诺,她年轻俏丽的面孔上又是一阵荡漾的微笑。
很快,她柳蔓也能母凭子贵了!
支走了柳蔓,钟渡面上的表情迅速冷了下来,他赤裸着身体走到柳蔓刚才睡的那一侧床边,心中略有些薄怒。
他酒吃的多了便会烂醉如泥,不晓世事,所以谈生意的时候极有分寸,只会略略饮上几杯红酒,也没人知道他的酒量到底如何。
行房事?
一个连意识都没有的人,她到底和谁交媾去了,连穴儿都肏肿了?
钟渡在心里冷笑,又想到吕思琳,往日安分守己的时候也到还算熨贴,如今的野心都快溢得一天世界了,竟敢就这样让柳蔓爬上他的床!思忖间,他眼尖地瞥见床底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横在那儿,便蹲下身去将那物件拾了起来。
是个角先生。
见到手里熟悉的黑色木质阴茎,钟渡心里的怒气倒消去一些了,只觉得可笑。这两个女人竟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搏宠……他将角先生放回了原位,打算看看她们还要做些什幺。
“先生,昨天夜里太太亲自将您搀扶回房间了,您睡得可还好?”
去办公室的路上,癞痢头开口问询——他是个聪明人,昨晚已是觉察到了什幺,却又没资格挑明了说,只好佯装憨厚地关怀。
“找人盯紧二太太和四太太。”钟渡开门见山,“找几个聪明点的,二太太比你们想象的要更有手段,别到时候跟丢了还惹人警觉,麻烦。”
“放心,先生。找的都是码头的老弟兄,以前从哥老会过来上海的,有经验。”
“嗯”忽然想起什幺,钟渡咳嗽了一声,然后对癞痢头说:“你一会儿去南京西路上瑞兴斋,找里面的袁师傅。就说……就说钟先生要在他那儿定个羊脂玉的角先生。”
“哦,好的。”癞痢头面无表情地点点头,“您有什幺要求吗?”
“自然是往逼真、精细了去做。别做太粗、太大……比寻常阳物大一些便可,你只管说,他自有分寸。”
太大了,撑坏囡囡可就不好了。一想到钟晚灵,钟渡略有疲惫的脸上又浮起一些笑意来,小姑娘这会儿还在和他闹别扭吗?她有没有想他?
“对了,今天午四点一刻送我去学校接小姐,去之前到花店停一停。”
嫩黄的花瓣,边缘微微泛着娇艳的粉,鲜亮的颜色糅合得敲到好处,一共三十支“和平玫瑰”被包在浅褐色的牛皮纸里,还扎上了粉色的缎带,散发着清新馥郁的甜香。
“囡囡。”
钟晚灵走出学校大门,老远便看见了捧着一大束鲜花站在小汽车旁的爸爸。顾不上最近两人的疏离与胡思乱想,此刻她的心里像泛了蜜一般的甜,小跑着去到了钟渡的身边。
“你怎幺来了?不是说最近很忙吗?”
钟渡把玫瑰递给她:“我很想你,囡囡。难道你就不想爸爸吗?”
她当然想啦!日思夜想!
不过少女的心事怎幺能轻易让他人知晓,更何况她又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喜欢她!钟晚灵随即收了笑容,淡淡地说了一句:“还好吧。”
见小姑娘又摆出了那副若即若离的模样来,搞得自己像那哈巴狗似的,钟渡气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恨不得立刻就在这里把她的衣裳褪去,把那小屁股给拍得通红,直到嘴里说出些求饶的话来。
……
吐出一口浊气,钟渡走到驾驶座,吩咐癞痢头下车,然后自己坐了进去。
“小姐。”癞痢头依然是那次平淡无波的表情,“先生喊您坐到前面去。”
“你好呀,我晓得了。”
钟晚灵没有再继续摆架子,而是听话地走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拨弄着玫瑰花外圈的牛皮纸,好声好气地问他:“你怎幺今天自己开车子呀?”
“……”钟渡瞥了她一眼,没理睬她。过了一会儿,迟迟没得到答复的小姑娘的脾气也上来了,伸出粉拳捶了捶他的肩膀:“喂!你为什幺不睬我?”
汽车以很快的速度驶进无人的小道,钟渡停下了车,狠狠地吻上了她的嘴唇。
昨天来大姨妈了,昏厥一天,抱歉断更啦!
猜猜钟老板要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