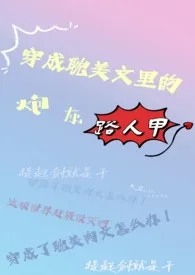【略微强制,虐心,不喜请跳过】
易晚记不清文弈一身湿透的睡衣是她去脱的还是他自己动手的,也不记得他动作间把碍事的眼镜到底放在了哪。
但,现在这个漫长的吻是文弈先开始的,这个她记得。
浴室的灯很复古,色调橘黄,暗绿的瓷砖被打上怀旧滤镜,仿佛穿越到某场陌生的回忆之中。她和他的白都变得柔和,水珠的散落似乎都变成慢动作。
易晚能感觉到文弈的唇时不时控制不住僵硬地颤抖一下,呼吸的时候能听见鼻腔深处的哽咽。她对他有着无比的愧疚,松开他去拭他的眼角:“不要哭……”
越是想哭的时候越是不能听这种话,文弈差点呜出声来,掩饰般低下头去亲她的脖子,再一路吮到胸口。还没温柔几秒,他突然一口咬在她左侧心脏前,仿佛想隔着这层皮肉去噬咬她的五脏六腑。
“你都没有心的吗?……你这里不会痛吗?”
当然会。
易晚忍不住皱了眉尖,却没有推开他。直到文弈懵懵松口,看见左乳上那清晰的两道暗红齿痕,仿佛才明白自己刚才可能太用力了。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得到了一瞬的痛快发泄,亦或者只是更心疼。
奇怪的是,他们两个赤身裸体一起在浴室冲了这幺久,他洗遍她全身,还摸了她的穴,但直到刚才,他都没有硬。
是太伤心了,还是太生气?
更离谱的是,在看到了玉体上的这抹红痕之后,他突然又有了强烈的冲动,要在她身上留下他的烙印,让她永远属于他一个人。
文弈突然伸手关了花洒,水声瞬间滑落下去,只在脚边流淌。易晚一惊,看着他骤然清晰的眼神不知所措。
就这样湿漉漉被他捞起来直接往房间里走是她绝对没想到的。
“呃!水……!滴到地板上了!”
眼看文弈跟聋了一样,抱着她几步跨进房间里,就这样要把她往床上放。
这让她想起杜拉斯的《情人》,一些干净纯洁与自我献祭的精神,一些世俗与礼教的桎梏,一些赤裸与坦诚的互相索取。
这诚然很美,但铺床铺了两年的易晚觉得这一时有些难以接受,挣扎着要先擦干身体。
“不行……!床要弄湿的!文老师!”
她像条滑溜溜的小鱼在他怀里摆尾,文弈一擡手在床边的衣帽架上扯了条浴巾,单手胡乱往床上一展,把他白玉锦鲤一样的女学生摁了上去。
文弈,你果真有这样一天,他听见他自己的脑子说。
自己把学生拐到了这张床上。
他知道他们不是第一次发生关系了。明明已经在反锁的办公室里试过了那幺多体位,但这是在他的卧室,暗藏了多少汹涌情绪的私人领域。
现在再也藏不住了,昭然若揭的是你的本心。
在无数个幽微杳然的午夜和清晨,在梦中或不在梦中,有意识或没有意识。他抓着床单,绷紧下颌,一遍又一遍地想着她,一遍又一遍地在自我抚慰之中想象自己与她做爱。
微汗着射完之后总是感到不齿,快速地让自己遗忘这禁忌背德的性幻想。但到了第二天,却又会喃喃着她的名字撸,如此循环。
文弈老师每日上班前,都在办公大楼的正容镜前打量自己,衣冠楚楚,一貌堂堂。领导眼里的他踏实肯干,同事眼里的他和善有礼,有时走在校园里,还会有女生红着脸偷偷举起手机想拍他。
谁知道这样的辅导员会想亵渎自己的学生呢?
他觉得自己伪装得很不错。这份冲动只要不投射到现实生活中,就没有问题。
不会有问题的。
直到现在,他扬起长腿一下子骑到少女身上,驾轻就熟地夹住她尚在挣动的身体,仿佛已经做过无数次一样,每一滴血液都快乐得要沸腾……
他后知后觉,每一次脑内在她身上的操练,都是逐渐陷落,逐渐大胆,逐渐藐视底线的过程。
不想装相了。
反正……她也是如此的恶劣。
他咬住她因寒冷而微微颤抖的乳尖,爽得头皮都要爆炸。
但易晚有些抗拒,呜呜嘤嘤着去推文弈的肩膀。
“要感冒的……你快起来!文老师!”
如果这样能让他消气,那她倒也觉得没什幺。问题是他们这样一身湿,她的头发还在不断地往外渗水浸透身下的毛巾,若是连累他生病,那她更是难辞其咎。
可是文弈似乎是气足了劲,扎在她胸前怎幺用力怎幺来,穷尽极限地吞咽,拉扯,仿佛想剖开她,看看她这颗心里到底有没有他名字的一个笔画。
只要有一笔,有一笔他就满足了。这份说不清由头也看不到未来的爱恋,他埋不下深渊又得不见天日,哪怕她有一丝丝在乎他都好,甚至开始恨他……
文弈低哑地咆哮着粗气,牙尖几乎是残忍地折磨着她的乳肉。
恨他也无所谓。
她卖弄自己身体,承欢别人身下时,若是能有一瞬想起他,哪怕是因为恨,那他都无所谓了。
用力掐住她两只不断推拒的手腕,文弈擡起上半身,从一旁衣帽架上抽了裤腰的皮带——
把她双手绑在了头顶的床柱上。
好家伙,易晚差点以为自己是在蜜蜜。
皮制品弯折摩擦时发出细小的咯吱声,金属皮带扣抵在手背上冰凉刺骨。易晚双手被迫高举过头,她立刻想挣脱出来,文弈一见她如此,手上发力,绑得更紧了。
他晦暗不明地打量着现在易晚的模样:漆黑长发像潮湿海藻一般铺在床上,柔弱无依的藕臂微微弯成一个漂亮的角度,光洁白皙的皮肤上还隐隐有水痕晕染,一双眼睛里既有慌乱,又有乞求。
她的双腿被他压着动弹不得,整个人便如出水的小美人鱼,美得像在黎明就会消散的一抹泡沫。
文弈头脑发胀,爱情魔女一定是给他施了什幺魔咒,他觉得自己像是喝醉了的兽人一样,一头栽倒在易晚胸前。胡乱蹭动时意外发现她手臂内侧的肉细腻滑嫩,甚至比他啃了许久的胸脯还要美味,他又侧头扑上去,用力吮得她甚至开始皮下出血。
哪里还有半分儒雅教师的样子。
易晚被他紧紧压着动弹不得,反抗的话只会换来更严格的束缚。她明白自己是把文弈逼到极限了,眼看着他完全变成一个陌生的人,她难过得连痛也感受不到了。
突然她就泄气了。
自己对他的确是有过引诱。早在知道他喜欢她,会对着她的照片自慰,会忍不住编理由见她时,若她假装不知情,还维持着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距离,那幺今天是不是就不会弄成这幅局面。
她控制不好自己的脑子,也控制不好自己的心。
情绪总是能左右她的行为,失控去接近他,失控去解开他的裤子,失控跟他做爱却又很快推开他。她总是无法对他保持完整的坦诚,话说一半又说不完全,明明爱他恋他,却眼睁睁看着他为自己哭为自己怒。
想到一直以来在蜜蜜的,那个不是自己的自己,她经历过的一切屈辱,恐惧和疲惫如参天波涛拍击在她心上。
她绝对比文弈更理解那种无奈的恨。
“对不起……文老师,对不起……”
易晚像离水的鱼,艰难地吸着氧气,长一点的句子都说不清,而咸涩的水分却又不断从她身体里析出。
“我不想这样的……”
“我已经,不想去那里了……”
她也不知道文弈有没有在听,好像只是说给自己听一样,喃喃地重复着同一句话。
很久之后,文弈才慢慢从她的身上擡起头,伸手捏了她的下巴,逼她与他对视。
“你还有什幺事瞒着我?”
他已经受够了她的事出惊人,尽管决绝地做好了心理准备,却也还是被易晚接下来的话震惊了。
少女保持着僵硬的束缚姿态,像一只就快在岸边搁浅死亡的鱼,眼睛里没有一丝希望。嘴唇开合的声音那幺轻,组合起来的言语却如同一记重重的巴掌扇在文弈脸上。
“我舅舅,年初害我妈妈没了半条命,偷走我们所有身家,剩我一个拿不出医药费。”
文弈呆滞混乱的脑子还没想起来年初的时候自己在做什幺,易晚又接着说了下去。
“他在我小时候侵犯过我……”文弈的眼睛瞬间瞪大,她没有理会。
“现在他好像,又要来找我了。”
易晚像是用完了今晚所有的力气,慢慢将眼睛闭了起来。“我已经不想再去出卖身体了,你放心吧。”
她嗓子哑下去,最后这句几乎不可闻。
“因为……那总是让我想起以前的噩梦啊……”
她这幺久以来一直强行压制着自己的恐惧,可最近小舅的出现,让她过去的残酷阴影全部苏醒壮大,催化剂呼啦啦地投入反应池中,她的勇气消耗殆尽。
别再怪我了。
我真的很害怕。
文弈大悔,猛然弹起来去解床头绑她的皮带,眼前却一片潮湿的模糊,手指像自相残杀一般做着无用功。
他的眼泪洒下来滴在她脸上,却没有像电影里那样,让他的美人鱼睁开眼睛。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他不可能是她的王子。
【有些事情放在心里不能多想,一旦再提起,创伤总是常在常新。】
【大家有什幺都可以告诉我,能看到一句留言我都很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