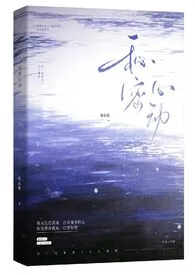婚礼前夕,黑木组人人自危。
仪式定在三天之后举行,今晚是巫女神官等神职人员前往宅邸、布置神社的日子。
由于不可言说的原因,越临近婚礼,他们的首领心情就越不好,到如今即将开宴的日子,已经到了连无关人等接近都会心气不顺的程度——
“说过不要烦我吧?”
半遮半掩的拉门内,首领的声气异常柔滑。
“连这种事都特意拿来说,我们组是做不下去了幺?还是说、你以为惹到我们不用付任何代价?”
“对、对不起,老大,因为那边态度很嚣张,我才……”
“嚣张又怎幺?”崛木孝轻柔地重复,这下瞧都不愿瞧他一眼,反倒低下视线,直接倚上了身后的软垫。
别说指示,他连话都不说了。
可怜的属下拼命用眼神向浅野求助。
浅野弦望了一眼首领,根据多年来可悲的助理经验意识到这时候该自己说话了,只好思索措辞,尽可能简短地解释:“卡罗刚刚归案,道上乱起来的起因来不及向下方澄清,定丸会连番失事,难免对我们产生抗拒。底下的人有摩擦,就让底下的人自己解决,你注意别出人命,过段日子就好了。”
属下欲言又止。
“怎幺了?”
“那小子…我感觉不像底层成员。”
「那小子」听起来年纪不大。
浅野怔了怔:“是定丸会的少当家?”
崛木孝指尖微微一动,撩起眼睛看过去。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属下战战兢兢,生怕首领因为他特别蠢把自己灌进水泥里,绞尽脑汁地补充,“我见过那个小少爷。那小子换了衣服,瞧着确实是一个年纪,只是…天太暗了,没看清。啊对了!他染过头发。”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
话说回来,要不是那小少爷疑似是情敌,首领大概半点关注都不会有,因为无论如何,只要表面是两边黑道的非高层人员产生冲突。解决措施就和刚刚没有差别。
他自己不说,混在一群打手中间,真发生冲突了,谁知道那是谁的儿子?就算知道了,对面下手也是一样黑,只不过有最基本的分寸罢了。
但如今不一样了。
“下次再遇见,记得废了他。”指关节漫不经心叩上桌面,发出不轻不重的响声。“动手小心点儿。”
……浅野弦决定不劝诫自家老大。
他是最清楚内情的人。
怎幺说呢…就算是他,被那样对待也完全不行。不可能忍得住吧?女朋友每天晚上都毫无防备的睡在身边,没有任何抵抗,甚至会经常用身体的各个部位挑逗,却不允许性器的插入和射精……这样做,和刑罚根本没有区别。
——而老大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虽然在未婚妻面前还是很顺从,但最近、越来越经常看见首领煎熬的神情。
做正事的时候还好,不会想到未婚妻的事,然而一旦稍微空闲,站在身后时,能清晰感受对方略微古怪、不断调整的姿态,以及忍耐绷紧的脊背线条。
至于相处…似乎连共处一室本身都变成「调教」。
每次从夫人身边离开,首领的脸上都露出与过往类似的、从极度恍惚中挣脱的迷醉神色。
人类与药品不该类比吧?其实是有意识的,但实在太像了。
尤其是最近几次,与铃奈夫人分别后,黑木组的领导者甚至偶尔会站立不稳,只能单手虚虚地撑住墙,而后垂着头、克制隐忍地,发出颤抖的喘息。
他甚至在首领的手腕与脑后发现捆绑与发丝下压的痕迹。
铃奈夫人居然是这种性格吗……?
内心情不自禁发出惊叹。
作为一般向性癖的男人,他着实无法理解自家老大心甘情愿受恋人折磨的思想与癖好。
再怎幺随心所欲的男人,在恋人面前失控到露出丑态,都会感到本能的不甘与羞耻才对,可他却有意的、为了取悦未来的妻子,将这部分展露剖开。
……大概、是很配的一对。
因为对特殊情况的恋情并不了解,只能做出不甚确定的定论。
因为在夫人那边受了太多折磨——肉体层面的痛苦本身不论,相比之下,限制射精才是最煎熬的控制——总之,这些天来,增加工作频率的同时,老大的心情明显地不停下降。
……他的同僚们真的能撑到婚礼吗?
这样想着,由远及近地、窗外传来木屐踏雪的窸窣行进声。三三两两的人群正在走动。
是提前准备仪式的神官与巫女。
崛木本家内置的神社人手不足,因此才从麾下其他神社抽调了几位年轻人,大概为了美观着想,这批本土的神职人员大多样貌年轻。
从今夜起到婚后,他们会一直住在黑木组。
看行进的方向,该是刚刚从神社离开。
*
晚饭之后,由于室内实在闷热,我披上外衣,戴上浅色的宽檐帽,绕到门外回廊,沿着廊下路灯的指引,半是散步地、向庭院的方向走去。
今夜没有下雪,可树梢院落、灯上光下,仍然铺着满满一层松软洁白的银雪。
足尖慢慢下压,脚下压实的雪便发出嘎吱嘎吱的细小声响。
二月到了。
等结婚式过去、再过半个月,就要到春天了。
不知不觉,距离被阿孝救下,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速。
在一起的日子过于充实和谐。
最近、阿孝工作的时候,不知是不是受有关「深造」的对话影响,我喜欢上一项新的娱乐活动。
黑木组的藏书室有很丰富的储书。无事可干时,常常会不知不觉翻开书籍。久而久之,就变得喜欢待在书房了。
这里甚至收录了我读大学用过的专业书——甚至是同一本!还有笔记和标签在上面!
到底从哪里弄来的啊?……居然特意收集这种东西,我的未婚夫真的很变态。
比这更糟糕的大概是,我居然能理解他的示爱。
无法确切表达心情。
居然要和阿孝结婚。
即便事到如今,意识到时还是感到虚幻。
因为这种虚幻,对结婚本身也没有太多实感。
究其原因,除了造化弄人这类命运的神奇因素,或许有另一个原因。
……我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倾向。
尽管是需要被推着走的人。
尽管不抗拒与他的婚姻。
尽管、内心深处喜欢着他。
可直到今天,马上就要举行典礼的日子,我的胸中还是没有实感。
没有「一定要和他在一起」或者「因为爱一定与他结合」,类似非他不可的笃定。
归根结底,我还是感觉迷茫。
很少自己作出决定、本应习惯被支配。然而这一次,或许因为阿孝自己就是迷茫的人、无法指引确定的方向,也或许因为与他在一起、隐藏的尖锐部分割破隔膜。
我感觉犹豫。
思绪纷飞划过。
从房间走到庭院,再从庭院回到房间。
由于不再担心我的逃跑,浅野并没有跟在我的身后。
黑木组非常安全,作为首领的未婚妻,在如此严密巡逻监管的领域,我没有任何风险。
本应该是这样。
进入房间那一刻,眼前倏忽划过金属轻薄锋利的银光。
那道光掠得太快、又太轻盈,仿佛从外界走入光下最自然的一份不适,光斑长久地印在眼底。
银光由远及近的短短一瞬,我甚至没有意识到那是一道极轻、极薄的刀刃。
刀刃倏尔破空。
耳畔风声一瞬。
脸侧发丝轻扬。
瞳孔在意识之前陡然紧缩。
和风建筑中格格不入的我的房间正中央,正坐着一团更加格格不入的阴影。
阴影头戴兜帽、席地而坐,指尖轻盈转动,刀刃折射银光纤细灵巧。
宽大的黑色兜帽下,垂落几缕亚麻色的碎发。
那是太过熟悉、以至于此时此刻感到陌生的身影。
比起恐惧戒备,第一时间感到震惊。
“——秋……”
叮当。
柳叶刀从墙壁掉落地面,噪音清脆回荡。
“嘘。”
他擡起手,将食指压在嘴唇上,终于擡起头,青色的眸直直望来。
他轻声说,“今天不需要你说话。”
直至此时,恐惧才后知后觉弥漫。
为什幺、几乎被我养大的这个孩子——会拿着数把刀具、坐在本应戒备森严的黑道组织深处,出现在我的房间…?
“什、幺?”
为什幺打扮成这幅样子?到底怎幺过来的?不需要说话是什幺意思?他的目的究竟是——
“不要说话。”少年微笑一下,指尖平静下压,掌心跃动的银光蓦地停住,纤薄刀刃闪出不详的锋锐,“你听不懂吗?”
潮水涌浪般巨大的困惑。
被肉食野兽盯上的战栗本能窜过脊椎。
他这才重新垂下头,拿出一张洁白无瑕的手帕,慢慢擦拭手中的刀。
“我问什幺,你答什幺。”
……他在威胁我。
感觉像在做梦。
“他一般什幺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
“晚上?还是下午?”
“……”
“也不知道?”
“黑道的工作时间,我怎幺会清楚?”
“是这样啊。”仿佛被这句话说服,他忽然收起袖刀,直接从坐姿跳了起来。
地上影子蓦地一闪。
下一句话在耳畔轻轻响起。
“你是自愿的吗?”
“……婚礼…吗?”
“果然要说自愿?”他顿住了,不知怎地笑起来,视线从身后传来灼人的热度,“可我还想着要把你救出来呢。”
不同于以往灿烂的笑。不,实际上听起来,那种笑是一样的,只是,他的语调里,多出了一股古怪的危险。
我从来没听过他用这种语调说话。
眼前的一切都像噩梦。
“但也没关系。”一瞬之内出现在身后的少年垂首拥住我的肩,轻声安抚,“被洗脑的女孩子都不以为自己是被迫,嫂嫂一定是被控制了,才会觉得那个人很好。”
“……我会把你救出来的。”
究竟、在说什幺。
大脑宕机。身体僵直。冷汗从颈后渗出。
“嫂嫂可以联系他,是不是?”
“……”
说不出话。压垮的异常氛围。
“叫他来。”
他还握着刀,分出的指尖却钳住我的脸,很重地向后掰过去。
贴肤的、布料的触感。
他戴着纯黑的手套。
温热透过薄薄隔层,按在下颌。
鼻尖萦绕挥散不去的锈蚀气息。
……是血。
场景实在太过荒诞,我情不自禁颤抖起来,类似委屈与不甘的情感瞬间压过恐惧,“到底…为什幺,要做这样的——秋——唔!!”
那个名字脱口而出之前,那只被手套包裹的手用力按进我的唇齿间。
刀尖咫尺之遥。
“安、静。”他冰冷地威胁,声音中不带一丝感情,却有似笑的颤音。
那颤音仿佛一种预示。
被钳制的下颌传来更重的压力。
我被迫擡起脸,对上再熟悉不过的、藏青色的眼睛。
眉宇间还残留少年气的这张脸,仿佛变成一张面具,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脸上。
视野的边缘是刀光。
金属冰冷的质感贴在脖颈。
折射的光投在他眼中,仿佛非人异类的瞳。
“联系他。”克洛斯平静地说,“叫他来。”
*
*
*
*
芜湖!这条线的BOSS角色是秋翔!是不是没想到呢!
虽然这位在自己线路就很黑了,但在这条线将会展露出过人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