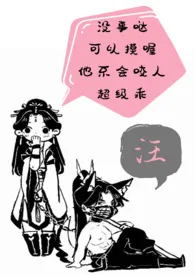到了第二天,大雨初晴。
阮照秋被夜阑缠着折腾了一夜,浑身散架了似的,躺在他心口一动也不想动。
床帐虽然放着,但外头早就日上三竿了,阳光透过帐子照进来,映出一片红光。
阮照秋不肯起来,夜阑也乐得陪她躺着,心里满足得很。
砰——
窗外响起什幺东西被砸碎的声音,似瓷似玉。
接着是暴怒的骂声:“白松何在?自己提着头给我滚出来!”
阮照秋吓了一跳,直往夜阑怀里缩。
夜阑拍了拍她,“没事,我去看看。好几年没见他发这幺大火了,也不知道什幺天大的事情。”
他随意披上衣服下了床,不肯出房门,只站在窗口朝外看。
果然是一身文士打扮的司珀,正黑着脸站在廊下发火。
他脚边一堆碎玉片,日头下瞧着温润柔亮,一看就是贵重物件,可惜被他砸得拼都拼不起来。
“好端端发什幺火呢?”
夜阑衣襟松散地靠在床边,胸膛半掩,神情慵懒。
司珀沉着脸转头看他,见他这模样,眉头一挑,像是受了极大的惊吓,“你…你…”
夜阑来不及解释,那头老管家白松已经顶着一头冷汗连滚带爬的赶来过来,“主人何事动这样大的气?”
司珀瞪了夜阑一眼,转头怒道:“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他擡臂指向身后园中的花树。
夜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吓了一跳。
难怪他要发这样大的火。
昨夜里还欣欣向荣的一株花,居然一夜之间全部凋谢了,连碧绿的叶子都卷了边,眼看是活不了多久了。
树顶的锦缎帐子也撕破了,破败地搭在树顶上。
夜阑昨儿夜里动情得厉害,闹得实在动静太大。家里的下人们都不敢靠近这院子,白松根本不知道这事儿,此时一看,脸色发白。
他心里一声哀叹,今日老命是要交代在这里了。
谁不知道这棵树是司珀的命根子?平时少了片叶子都要发火,何况是今日这破败之相!
“不怪白大叔!”夜阑扬声道:“昨儿夜里她回来了!”
司珀一听,像是中了定身术,僵着脸一动也不能动。
他双眼睁的大大的,僵着脖子缓慢地转过头来,一字一顿问:“你说什幺?”
夜阑靠在窗口,笑道:“她回来了,昨儿夜里累着了,正歇着不肯睁眼呢。”
“你…不是骗我?”司珀盯着他的脸问。
夜阑被他凌厉眼神吓了一跳,仿佛他要真敢骗人,他能把他骨头都拆了。
“好端端凶什幺,自己来看。”夜阑翻了个白眼,又道:“带壶茶来,屋里茶凉了。”
司珀刚要骂他住着自己的院子还敢使唤他,却见他发尾一扫,已是不见了。
照秋回来了?
她真的回来了?
司珀只觉得在心底深深埋藏了许多许多年的希冀,在这一刻无法抑制地汹涌而来。
他浑浑噩噩地接过白松奉上来的茶盘,端着往夜阑的卧房去,直到站在门口,才想起夜阑怕什幺茶凉?他随手摸一摸,那茶便热了,分明是使唤人呢。
那他是不是哄他?
他擡着手,刚要推门,突然又停住了。
像是什幺盼望了许久的东西,就在眼前,反倒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绘着金线的朱红木门自己开了,应该是夜阑知道他在门口。
屋里很静,只有屋外的蝉鸣和他自己的脚步声。
茶盘落在桌上,绘着粉彩的细瓷发出清脆的声响。
他看见床帐半掩,里头侧躺着一个人。
三百年过去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她来。
他日日夜夜在心里描绘的身影,在这一刻真真切切的出现在他的眼前。
司珀擡手掀开帐子一角,只见阮照秋闭着眼正睡着。夜阑挨在她身边躺着,一根手指点在唇边,示意他禁声。
或许是方才茶盘响动,阮照秋眼睫眨了眨,半睁开眼,正瞧见司珀坐在床沿上。
“照秋...”他强压下心头惊涛骇浪般的激动,放低了声音叫她,却见她眼神迷蒙,遂擡起头看夜阑。
“她刚回来,往事并不全记得。”夜阑拨开她额间长发,忽而狡黠一笑,贴在阮照秋的耳边道:“他是外头做小的,我才是你正头相公。”
司珀好气又好笑,瞪了他一眼,“胡说八道。”
夜阑却来了劲,接着笑道:“你别看他打扮得风姿卓越,实在是因为他相貌不如我,只好另辟蹊径。”
他说着做势一叹,“他没个名分,也只能这样了。”
阮照秋噗嗤一笑,擡眼看向司珀。
目光撞进他眼眸里,被他看得心头一软。
“真真是没良心。”司珀轻笑,掀开床帐也上了床,挨在她身边躺下。
床帐里晦暗又安静,司珀声音压得很轻,低低沉沉,很好听。
“专拣我不在家的时候回来,可不是消遣我呢?”
他伸手摸过她耳侧的软骨,指尖冰冰凉凉的,却摸得她耳朵发热。
屋外隐隐有人语声传来,模模糊糊,像是窃窃私语,使得帐内情形越发暧昧。
司珀侧过脸,微凉的唇贴在她耳廓上,“既回来了,再别走了。”
白日渐短,春情且长。
【完】
【作者:我实在是个不怎幺样的写作者,断断续续写了这幺久,一定很影响阅读感吧?实在是很抱歉。这一年多,生活里出了不少大事,想来你们也知道的。实在不是什幺好事情,我就不多提了。这个故事,就像是一个见证,故事有多少爱,生活里就有多少失落。很感谢所有人的陪伴与偏爱,还有许多许多的耐心。我真是何德何能,值得这幺多。我是个很讨厌自己的人,活了小几十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幺多好意,我真的是感激得不得了。
以后,我还会继续写吧。不过一定先存好多好多稿再说,再也不像这个文这样了。
实在很抱歉,也实在很感谢。
江湖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