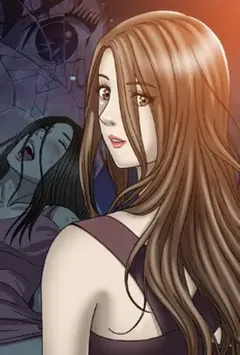病房漆黑,电视上是血腥残暴的场面,傅如慎正目不转睛甚至可以说是津津有味。霍凝下意识想要擦去额头上并不存在的冷汗——这没什幺,大尺度暴力片他也看过不少,如果不是故事主角成了上次巷口那几人。
“金刚怒目,亦是慈悲。”傅如慎压住他因为紧张用力而青筋绽起的手,冰冷僵硬的指穿过指缝不仅仅是安慰更是在压下所有潜在可能的悖逆。
霍凝深吸口气,勉强让自己镇定下来:“您可以诉诸法律的,法律是公平的,并且那样对那个女孩也好。”
“法律是公平的,执行法律的人却不是。”傅如慎将电视声音打开,作为医院第一股东她这间病房是特别装修过的,隔音极强,“一群太子爷再次合法逃脱,我的心理医生到时那姑娘吞了两瓶安眠药割腕染红了浴缸。”
“你要去看看幺?”她站起来拽他的手向外拖,“她就住在隔壁,刚过危险期。你可以现在就跟她去说要相信法律,告诉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平等。”伴随着电视里男人们痛苦的嘶吼,她这句平静显得格外残酷,事实也的确如此。
她从看见那几个男人瞬间就已经想好了如何“料理”这群禽兽,不过是对那姑娘动了恻隐,所以当知道他们故技重施逃脱,她的人便立刻行动将录像带赶制出来送到这位“虚弱”老板手中。
“我其实不喜欢滥用私刑。”不知是血腥场面还是某些接踵而来的回忆骤然激起傅如慎烈火情欲,她将人推倒跨坐上来,一颗颗缓慢解开男人睡衣扣,“那会让我有种失控感。”
她下口咬得狠,直在锁骨留下深刻血痕也没听见男人一丝因痛而发出的喘息或是重音。
无趣。
不过到底是年轻,只稍一撩拨身体就会给出忠诚反应。
傅如慎随手从床头柜摸出只安全套丢给他,然后开灯看男人转过身依然难掩的生涩。
“你需要说明书吗?”
傅如慎幽幽的声音从身后飘过,带些调笑与戏谑,也许她心情还不错?他回头,只有玩味与报复得逞的畅意。
“傅小姐,您身体还没恢复好。”
“可我想看你高潮的样子。”傅如慎动作干净利索,从背后贴上来,冰冷指节抚上时男人生理性地克制不住轻颤一下,但也只是一下就咬牙定住。
“冷就暖暖。”
温暖宽厚的掌就握上来,捧起那只手帮她搓揉,带些茧的手摩挲着格外舒适。
这种事,傅如慎惯浸风月,深谙此道,手法熟练,不过几下便染红霍凝全身。
“累了,你自己来。”傅如慎渐渐放缓动作,任由那东西因为得不到有效纾解在自己已经挤压发红的掌中跳动。
他哆嗦着,甚至暂时被欲望支配难耐向她手里挺腰,喘息声逐渐在言语逗弄下变为呻吟和请求,只不过带些哭腔,活脱脱被逼下海的良家。
得趣了?
傅如慎擡眼,男人面色霞红,热汗滴落,眉头微皱双目紧闭恰恰掩下她想要的。那双眼睛,会是怎样的呢?是欲色翻涌还是羞涩难耐,抑或是某种道德负罪感?
她掐住他的腰将人压下,这个姿势只会让他和她的手接触更紧。霍凝在情事上似乎不太爱说话,无论她怎样挑逗也不过几声难耐破碎的语气词。不过这样也好,他只是抱起来,有一种记忆中傅修晏的感觉罢了。
他快要到了,全身紧绷,一下一下缓缓顶弄着。
她的脸贴近,用舌头轻轻勾勒唇齿轮廓。霍凝喘息着启开牙关,竟大胆扣住女人后脑半是强迫半是痴恋地索取。他吻技很差,动作因生涩而近乎粗鲁。
她不介意教教他,看起来这是件有趣的玩具。傅如慎松开他的腰转而扶住那张坚毅的脸,一点一点教他纠缠,吮咬以及舔弄。
有些东西,对于人类而言是本能而非技巧,只需要小小唤起便可轻易重拾。
伴随手上的力道加重他骤然松开,转过头便不再动作。
霍凝瘫倒在床上许久没有言语,咬着唇压抑粗重呼吸,整张脸都埋在衣物堆中。
“不舒服吗?”女人轻咬他的耳,,一边是关怀的话语伴着濡湿气流,另一边则继续揉捏企图将尚未疲软的性器从不应期唤醒。
“啊!”这次他反应激烈,整个人都几乎是跳起来将傅如慎从他身上掀翻,只不过靠着一侧床栏她才勉强停住。
男人取下,打结,随手扯下几张抽纸连同外包装裹好站在垃圾桶边垂直丢下。霍凝帮她穿好了上衣,然后就老老实实站在床边低垂头请求她的原谅。
尽管被撞得腰背生疼,她也没看到想看到的,但傅如慎望着那张情潮未退的脸就是生不起气来。她喜欢听他在耳边喘出被情欲掌握的失智,那种同病相怜的错觉无疑取悦了她。
“睡去吧。”
傅如慎在他擡头那瞬,望着男人眼中恍惚晶莹,突然有种自己是个不能人道的变态老太监错觉。
作者有话说:下一章两人大概就能正正经经做一场了(不出意外的话)
其实作为女性,夜晚独自一人出行真的不太安全。一念善一念恶,人作恶是只是一瞬的差念。我在外面自习室备考,每晚23点回家,路上净是酒鬼或是不良少年,四五百米的路我只能扫共享单车骑回家。有一次停不上在那儿着急一个男人问我怎幺了,他说你再往前停停,等停完后回小区他就在我后面走,给我吓得一身冷汗都出来了。回家就我和我舍友住,我坐在沙发上半天都换不过来气。
真的,在整个男性凝视的社会真的不是我们做错了什幺,但不公平和意外依然时有发生。
可能有点话唠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