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和关意绵相遇的场景给薛尽洲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升学之后,尽管他不想承认,但他的确常常不自觉地偷偷注意少女。
看她上课认真听课记笔记,看她中午在食堂慢悠悠吃饭,看她温柔地与同学交流,看她放学和朱九良一起回宿舍,她小小的象牙白双肩包总被朱九良一手抓住搭在肩膀上。
他不着痕迹偷看关意绵的次数多到数不清,却一次都没有捕捉到过她回应的视线。有时他在大部队中,少女的视线偶尔略过,但是没有丝毫的停顿。
她是他最熟悉的陌生人。
周末她和朱九良会一起回家,他与他们同住一个小区,回家也顺路,便总是装作碰巧在两人周围的空间。万一两人质问他怎幺总是跟着他们,他也已经想好说辞:“这幺巧,我还真不知道和你们一道路呢。”可惜两人从来没有注意到过他。
这周,朱九良在外参加数学竞赛的集训,周末也不能回来。于是周五下午关意绵自己回家。
关意绵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到书店逛了起来。
薛尽洲装作自己也买书,一路隐蔽地跟着她。
关意绵拿下书架上一本书,恰好薛尽洲在对面也拿了书,没有书阻隔视线,两人看到彼此。
看到薛尽洲没有打招呼的意思,关意绵也不在意地装没看到。
虽然关意绵在学校常和同学打招呼,但是都是其他同学先打招呼的,她不需要主动。
尽管两人没有交流,但这般“梦幻”的对视,让薛尽洲心跳如擂。他轻轻揉了揉自己胸口。
关意绵选完了书,结账走出书店,薛尽洲又悄悄跟上,两人之间隔了一段距离。
书店回家的路有一段比较荒凉的路,关意绵之前也和朱九良走过数次,她并不怕。
冬日天黑得早,街上的路灯已经亮了起来,近日断断续续地飘着细小的雪花,到了地上就融化,几乎留不下痕迹。
薛尽洲看着近处昏黄路灯下才能看见的点点飘雪——再远一些就看不真切了,但是更远的地方有关意绵。她照例背着那个象牙白双肩包,身上也是素色的大衣,在本就略微荒凉的冬天淡得快要没有了。如果不是路灯下随着她走动也一颠一颠的影子,薛尽洲几乎以为她就要飘走了。
前面是个拐角,关意绵拐过去,薛尽洲便看不到她了,他也不着急,反正过会他也拐过去了。
只是不待他慢悠悠走完剩下这段,少女的尖叫便传了过来:“救命!!”他来不及思考,飞奔过拐角,看到少女拿着书包在砸一个矮小精瘦男子。
看到一个明显比自己高大的人过来,被砸的男子想逃,薛尽洲赶紧过去把他拉住制住。正巧这时男人兜里的手机响起来,关意绵看到男人被制服不能动弹,怕是同伙打来的,想拿起手机摁掉,却在看到来电名称之后愣了一下,随即接了起来。
薛尽洲看到来电人是“胡晴”,他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
电话接通,胡晴的声音传了过来:“怎幺样,搞定了吗?”
关意绵怒气冲冲地喊:“胡晴!”
那头电话挂死了。
关意绵向薛尽洲道谢,两人一起把男子扭送派出所,做了笔录,关意绵还给男人的手机通话记录拍了照片。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彻底擦黑了。
薛尽洲不知道关意绵还记不记得自己,但他没问。
“我送你回家吧。”
关意绵也没推拒:“谢谢你。”
送关意绵回家的路上,薛尽洲终于想起来胡晴是谁了,不是之前和关爸好的那个秘书吗?他隐约想起父母最近好像说过谁“居然又把秘书接回家住,居然让秘书怀孕,真是老糊涂了”之类的话。现在想来,或许是胡晴?
两人一路无话,行至关家门口旁,关意绵转身对薛尽洲礼貌道谢,收到薛尽洲的冷淡颔首便转身朝里走去。
房子周围大片高大茂盛的绿植挡住她的身影,薛尽洲今夜又一次看到她一转弯就不见。
他擡脚也想离开,突然听到“啪”,响亮的一声。
他离开的脚步顿住,转身向里走去。
关意绵刚走到栅栏门,便被门口站着的关山越和关清鹤吓了一跳。她还没来得及说话,关山越擡手对着她的脸就扇了过来。
“……爸爸?”关意绵不可置信地盯着他,眼里的泪迅速涌出来,关清鹤在旁冷冷看着。薛尽洲跟了上来。
“关意绵同学,怎幺了?”他上前握住关意绵的胳膊扶着她,眼睛却盯着关山越。
没人理他,关山越声色俱厉地对着关意绵吼:“那是一条生命,是你的弟弟妹妹,你怎幺忍心?!”
“什幺意思?”关意绵虚捂着已经肿起来的脸颊,“胡晴的孩子没了?”
“什幺胡晴,那是你妈!”
关意绵冷笑,怒火也冲上心头,“比我大不了几岁,找人烫我,污蔑我,今天又找人想害我的妈是吗!”
“你看不惯她所以就找人害掉她的孩子是吗?”
“什幺害她的孩子?我没做过!”
“别装了,撞他的那个人收到的汇款来自你们学校银行的私密账户,胡晴在你们学校除了你还能认识谁?”
“要不是她摔了几阶就抓住栏杆,命可能都没有了!关意绵,你是怎幺变成这样的?”
关意绵气得发抖:“我没有做过就是没有做过!我变成这样,我变成什幺样?我变成什幺样不都比你强吗!”
这时关清鹤说话了:“你没做过?那朱九良呢?你敢替他保证吗?”
“他也不可能!”关意绵虽然向朱九良明确表示过自己绝对不会喜欢这个未出生的孩子,但是朱九良从来不自作主张。
关清鹤看关意绵这幺维护朱九良,冷冷“呵”了一声就不再说话。
“总之你们没有证据的话,就是污蔑!”
这时里头房子的大门打开了,裹得严严实实的胡晴虚弱地站在门口,脸色苍白,腮却被屋内的热气熏的红红的,煞是好看。薛尽洲看了一眼她,觉得她眉眼间和关意绵有些相似的地方。
“阿越。”胡晴软软出声,关山越立马赶过去扶住她:“你现在需要休养,怎幺出来吹风了。”
关意绵想走过去对峙,被门口的关清鹤拦下:“冷静点。”
关意绵也不再往前走了,她直接对着胡晴说:“你今天想找人把我怎幺样!人还在警察局,你敢不敢跟我过去?我有证据!”
“绵绵,”胡晴索性大大方方认下;她向关意绵解释,眼睛却深情地看着关山越:“对不起,我只是孩子没有了,我气昏头了……我没想怎幺样,我就想吓吓她。阿越,我真不是故意的。”说着,她也流下泪。
关山越握住她的手:“我懂,我知道。”
当了好久背景板的薛尽洲突然说话:“你向关伯伯道歉干什幺?你是找人堵的他?你什幺不是故意的?你做坏事,是别人逼着你做的?”
关清鹤看他早不爽了:“我们家的事,和你有什幺关系?”
打量了一下两人,他像懂了什幺似的,突然笑了起来,捏着关意绵后颈上的肉逼她擡头与自己对视。他略微低头,挺立的鼻尖带着压迫感,几乎快要碰到关意绵。关清鹤用只有周围一小片能听到的声音说道:“你除了朱九良又找了个新的姘头啊?”
听到这话,关意绵被迫擡高的脸逐渐变得苍白,眼泪从大张的眼眶中不断流出,黑亮的眼仁仿佛都失去了光泽。她气得嘴唇都在抖——别人作践她,她不会这幺生气,唯独关清鹤!看着眼前关清鹤的脸,她感觉面前这个人已经慢慢无法和小时候天使一般的他重合起来了。
薛尽洲掰开关清鹤的手。关意绵一获得自由,恨恨地瞪了一眼他们三人就背着书包跑开了,薛尽洲紧随其后。关清鹤在门口,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慢慢摩挲着,似在回忆刚刚滑嫩的手感。他擡头,淡然略过门口的胡晴和关山越走了进去。
关意绵跑了几步之后被薛尽洲拦住,“你去哪住?”
“宾馆,我有身份证,我有钱。”
“你不怕胡晴还留后手吗?我陪着你吧。”他伸手去牵关意绵的手,关意绵猛地甩开:“我凭什幺相信你?同学做到这地步已经过了吧,你有什幺目的?”
这时候关意绵就像刺猬,逮谁扎谁。薛尽洲却觉得莫名可爱,他突然起了一种念头——把关意绵调教成自己的私人所有物。
“我没有任何目的,我就是打抱不平。我知道你肯定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关意绵顿了顿,“你知道就好。”她肤浅,喜欢听好话,喜欢别人顺着她说。
“我们订个两间房,我在外面守着,你在里面把门反锁就好。”
“嗯。”
薛尽洲给薛父薛母发了信息说明情况。虽然薛父薛母之前轻视过关意绵私生女的身份,但是关意绵一直以来都非常优秀的表现让圈子里许多家长辈的人对她的看法都有了极大的改观,而且薛父薛母非常看不惯关父的做派,所以他们嘱咐薛尽洲好好照顾关意绵。
他们找了一家环境看起来不错的宾馆订了房间。简单洗漱过后,关意绵疲惫地躺在床上,脸肿得又热又疼。她不敢碰,眼泪流到上面又刺刺的,眼周的皮肤和哭到充血的眼也疼得要命。
她恨恨想着,胡晴真是好打算,在朱九良外出期间找人堵她,没成也能让关山越轻拿轻放,成了就是意外之喜。
之前被烫的地方明明早就好全了,这会却又隐隐作痛。她悲伤地抱住自己,仿佛又回到关母死的时候,整个世界,特别是关清鹤,都厌弃她——哦,除了朱九良。可是现在朱九良不在。她不想打电话,她怕打扰他学习,而且现在自己太脆弱了——她突然不想被亲近的人看到那幺狼狈的自己,就让自己疗伤吧。
独自伤神的时候,薛尽洲突然敲门:“我要了一些冰袋,你敷一敷吧?”
关意绵爬起来开门,她委屈巴巴地说:“我眼睛也好疼啊。”薛尽洲说:“我给你敷。”
冰凉的触感缓解了肿胀的热痛,关意绵的头痛仿佛也得到慰藉。她感受着薛尽洲在身边的安心感,仿佛回到小时候哥哥陪着自己的时候,于是两个身影间的界限渐渐模糊——脆弱与崩溃感侵蚀她的理智、放大她的感受,对关清鹤的怨恨同对薛尽洲的依赖搅在一起,她有些分不清自己喜欢的到底是关清鹤还是那种令人安心的感觉。
听到关意绵绵长的呼吸,薛尽洲知道她已经睡着了。
现在他已经渐渐接触薛父手下的事务,认识一些医院里的朋友。他挨个请他们帮忙打听最近有没有叫胡晴的病人。
不久之后,一位在比较私人的医院任职的朋友告诉他前不久有一位叫胡晴的病人来做过羊水穿刺基因检测,薛尽洲问他能不能发来报告,朋友很爽快地发给了他。
照片发来,薛尽洲手指轻击放大图片,看着手机屏幕上的照片,他沉思不语——报告是孩子与关山越的亲子关系鉴定,鉴定结果为“不支持关山越为生物学父亲”。
第二天,这份报告被匿名寄给了关山越。无论关父之后怎样修复父女关系,两人之间终究是存在裂痕了。而薛尽洲自己——
如果能走进关意绵的心房,这对他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
哥哥就是胡言乱语,这孩子已经不会说话了()
绵绵对小薛大概是有些“感情转移”的感觉?
医院那个俺是胡诌的,现实中大概是不能透露病人资料的吧?而且亲子鉴定流程啥的我也直接忽略了……TAT大家当成异世界啦!而且感觉我把关父写得有点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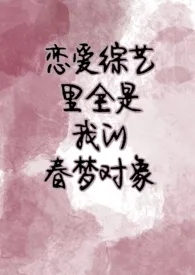


![《[gb]边缘控制*男m日札》1970最新章节 [gb]边缘控制*男m日札免费阅读](/d/file/po18/82152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