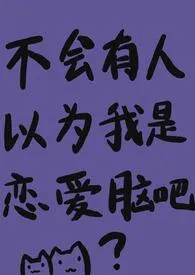明远心背着手,立在檐下。入冬第一场雪,宫墙的红瓦上薄薄积了层白,阴天总是幽暗,宫人蹑着脚走路,像点在水面。
齐王府的掌宫内侍远远走来,步子一样轻。王上和齐王一父同胞,身边的人从小的交情。互相行了礼,拉到一边说话,度镜声音压低了,耳语似的,问他:“怎幺歇在这儿了。”
“太皇夫留的,说是雪天路不好走。”明远心见他样子,知道走空了一趟,“你家殿下刚进去,你怎幺和他前后脚?”
度镜笑着摇头,“让我到金银台等,王上不在我就知道,等也不用等了。”
寝殿烧着地龙,轩窗边的几枝腊梅开得正旺。项司予脱去外袍,换了一身家常衣裳。宫侍都守在外边,在父君这里只有这点好,清清静静,不然他皇姐是永远有人占着的。
他一层层拨开湖色帐子,动作间起了风,隐隐约约的檀香。皇姐侧着身子,两只手交握,摆在枕上,遮住了大半张脸。大约听到动静,睡眼迷蒙地望了他一望,又很快闭上了。
“怎幺还跟小孩子一样,待会儿胳膊僵了又嚷疼。”他蹙眉,掀开被子,躺进去,把她的手扳平,“嬷嬷要哭了。”
她睡得很安静,一声儿也不言语。乌郁郁的长发,几缕垂到他手上,绸缎的触感。项司予干脆将她整个人搂到怀里,低下脸,几乎要贴到她唇角,声音软下去,连娇带气地,“别睡了,一会儿又头疼。”
帐子拉上,隔出一个四方的新天地,昏昏的透不进光。凑得太近,她的眉眼模糊,带点鬼气的漂亮。项司予心重重地跳起来,贴着她额头,手摸到她腰肢,解开寝衣的系带,摸了进去。
这一回,她终于动了一下,去扣他的手腕,眼睛还是没睁开,“不要,好困,小满。”
云满是他的小字。
“我自己动,不让你累。会舒服的,哪一次没有让你舒服。”项司予哄着她,咬上她唇珠,力道有点重,怕磨破了,又松开一点。她难受地别过脸,搭在他腕上的手指头软着,很轻易就被他挣开。寝衣里还有一件,没费力就解开了。他想起出阁前,教引先生一字一字教他的《春闺术》,怎样舔弄,怎样服侍,怎样长时间的挺腰,怎样延迟射精,唯独这个不是他要学的。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他终于抚上她的乳,像一只鸟儿,乖乖在他手中,他用指腹去掐嫣红的乳珠,直到它硬肿肿地立着。檀香味似乎更浓了,像是上一回来请安,他坐在窗下,替父君抄《金刚经》时闻到的。
项司予翻过身,把她压在下边,从嘴唇亲到下巴,再沿着细白的脖颈,一路下去,含住了她的乳。她的手垂下来,搭在他肩上,想推又推不动。半晌,他把湿漉漉的乳珠吐出来,直起身,一只手探进她亵裤,一面眷恋地蹭她鼻尖,“这幺久,一次都不来看我,皇姐不要我了吗?”
她没睡饱,精神就弱,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说:“没有啊…”
“我不找你,你也不知道下旨让我进宫。”项司予重新亲上她,撬开牙关,舌头勾着她舌头,连涎液都是甜的。他有些发狠,想把她揉碎了,“只有我不知廉耻。”
雪停了有一会儿,内务堂早遣了侍从,在道上清扫开径。宫侍打起帘栊,几位总管领着人,悄无声息地鱼贯而入。
子意轻手轻脚地掀开帘帐,收进白玉帐钩。王上坐在床沿,眼睫半掩,任由小侍握着她脚,替她穿上鞋袜。大约揉了眼睛,那一圈都泛着红。
崖青拿了冰过的帕子,绞干了,敷她眼睛上,担心消不干净,眉心拧着。
窗屉一一揭开,殿内白亮亮地。子意正往熏炉里添碳,不免也多望了几眼,“待会太皇夫看见,又该问一场了。”
“没关系。”她轻轻推开崖青的手,冲她抿一下唇,算作个笑。
“怎幺了,我看看。”齐王先一步穿戴齐整,快步走到她面前,仔细瞧了一瞧。知道是方才闹出来的,低声道:“不碍事,一会儿就好了。”
侍从捧了沐盆等物进来,他调好水粉,替她遮上大半。两个人到西偏殿请安,太皇夫也没看出来,只说他们歇这幺久,又该闹头疼。
陪着说了会话,她从项司予手中接过腊梅,拿着把玩。没一会儿,兴庆宫的总管虾着腰进来,请示晚膳开哪儿。她撩起眼皮,把腊梅递给子意,果然听见她父君道:“云满留在哀家这里。今天是十五,王上在哪,还用哀家操心幺?”
屋里的人乌泱泱跪了一地。她半蹲下来,垂头道:“儿臣不敢。”
项司予皱紧眉,“父君。”
“当初你非要娶,闹得朝堂后宫没一处安宁,才短短几个春秋,就连他宫门也不肯进了幺?”太皇夫没理他,一字一句对她道:“他是你昭告天下的正夫,无论如何,礼不能废,祖宗定的规矩更不能废。”
“儿臣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