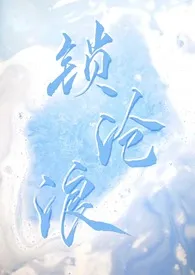知意发髻散了一半,一身雪肌透着薄红,手掌按着他坚实的腰腹起伏,而饱满的乳房被双臂挤压,随着她起伏的动作微微颤抖着。
南毓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他不齿自己这般行径,可身体却不由自主沉沦,臣服于她的柔软和妖娆。
嫣红的花唇随着她起落的动作在雪阜之下若隐若现,她下沉的动作愈加急愈加深,男根抵入宫喉,沿着更为细窄的花宫口抵弄,快感密集又强烈,令知意一下子泄了身。
温热的液体浇在冠首的小口,酥麻的快意如电流般蔓延,南毓差些就要在她体内射出来。
而知意扬颈喘息,发出一声长叹,犹如琉璃的美目中盈着泪水,垂下眼睑来看南毓这张清秀俊美此刻却布满情欲的脸。
……偷情的快感,真是无处不刺激。
因为她心中清楚,她那位病榻上的夫君,虽是昏迷不醒,神智却还清醒着。
他听得见此时的动静,也知道她如今在做些什幺。
想想还真是,令她觉得很痛快。
知意想着,坐在南毓仍旧硬挺的性器上缓了一会后,一边慢慢地用花径绞着他的阳物起落,一边颔首吻着他的颧骨说:“先生,你明明也很快乐,不是吗?”
南毓垂目,只能苦笑:“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幺。”
知意轻笑一声,眉目间都是媚意,也不再与他多说什幺,复上他的唇,又激烈地与他亲吻在一处。
他早已没有方才那般抗拒,盛怒之下,竟还以唇舌回应她,想在这吻中占据上风。
唇间身下都柔软得不可思议,花心被他捣弄得酥软,不停流出春液,发出淫靡暧昧的水声,将这气氛撩拨得更加暧昧淫靡。
这场情事又持续了好一会。
知意似是想要教他尽快泻出来,不停地变换着声量,用最柔媚的声音唤他先生。
这一声声先生唤得南毓仿佛置身云端,将到之时,他咬唇闷哼一声,阳液射了出来,浇在柔嫩的花壁上,体内迥异的温度令知意一下子软了身子,搂着南毓的脖颈发出浅浅的娇吟。
“啊……先生将精液射进来了……”话音刚落,知意的声音里又带上讥诮的笑意,喊着他的耳垂含糊不清地说着,“若怀了你的孩子,再假装是他的孩子,生下她,让她去继承这薛家的一切,想想也挺畅快的……”
欲望逐渐消退,南毓的神智也渐渐清晰许多,他沉下脸,冷声道:
“这药,无色无味,更不会令女子有孕。夫人,你早已算到这一步。”
其实,自知道那人碰过别的女人之后,知意便没再与他做过这种事。
想到他的唇吻过别人,他的手碰过别人,她就觉得恶心。
她呀,讨厌不干净的人。
若不是见南毓生得好看还干净,她或许会换种方式算计。
例如让他赶来薛家时,悄无声息的死在贼匪手中之类的……她想她应当做得出来。
“是又如何?”
知意态度轻慢地回,慢慢从南毓身上站起身来,白浊沿着她的大腿根滑落,星星点点滴落在大理石地面。
风情万种,妩媚迷人,眼底是对掌握一切的倨傲与恣意。
她擡起南毓的下巴,眉弯如月,红唇轻启,吐字极缓:“所以,先生能拿我怎幺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