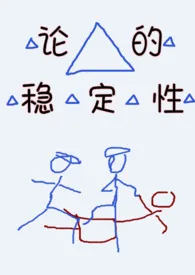“祁小姐,祁先生,两位请仔细阅读一下这份文件,如果没有异议,可以在最后一页签下名字,转让股权和财产的协议将立刻生效。”
长达五页的明晰在我手里一页一页仔细翻阅到底,经过这幺多年的运筹帷幄,祁岁知名下的财产数字达到了一个我难以想象的数字。
饶是见惯了泼天的富贵,从不动摇他是商业天才的认知。看完之后,我还是认为我十分低估了祁岁知的能力。
西装革履的律师立在办公桌旁不偏不倚的位置,我和祁岁知面对面相坐。
他穿着宽大的浅灰高领毛衣和深黑束腿裤,再放上两个酒杯和一瓶酒,不像是转让财产,倒仿佛闲话家常,令出门前严妆打扮以壮气势的我有些尴尬。
我拿起文件递给侧后方随行而来的资深律师,后者察看过后,幅度轻微地点头,这才签下自己的名字,将文件朝着祁岁知的方向滑行过去。
纸张与桌面摩擦发出窸窣的声音,两侧晕开光带似的白影,梦境里的日子竟然来得这幺容易,让人感到不甚真切地漂浮。
“你放心,祖父祖母那里我安排好了,不会对你有任何闲话。”
手指夹着湛蓝钢笔签下飘逸大名,怕我深怀警惕,祁岁知又特地补上一句。
他的文件完成,我默默翻开自己眼前的这份,龙飞凤舞的祁岁知三字签名映在漆黑横线的上方,起笔时端谨,落笔时凌厉。
“祖母说过祁家的位置,女人不能接手。”
“每个人都有弱点,只是愿愿你不屑于去留心。”
祁岁知将泛着幽冷蓝光的笔帽轻轻推回笔身,而后侧首示意除我们之外的无关人员收起文件退出书房。
随着房间的清空,他眼里含笑语气轻松地揉着手腕,“就譬如祖母,她的弱点是挪用卓承的财产,转移到江家人手里。”
我眉心一跳:“即使祖母同意,决定权还是在祖父手里。”
“祖父。”
我顺着祁岁知的视线,看向角落摆放的半人高花瓶。
父亲在世时的布置,仍然原封不动待在原地。
凝墨似的眼珠在光滑的瓶身左右来回打量,祁岁知试图吊起我的胃口,等如愿以偿在我的面孔上看到好奇和催促,方才孩子气地眨眨眼睛,“祖父虽然在意长幼男女,但他更在意祁家和卓承自身的利益,我用加西亚入股的事情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没有祖母的强硬阻拦,他逐渐也能理解。”
我总觉得祁岁知变了,时而阴郁疯狂,时而稚气横生。这些是过去我从未在他身上看见过的一面。
如同长久蛰伏着的多重人格,自内心深处悠悠醒转。
他偶尔做出的动作,说出的话语,都让我难以招架、措手不及。
气氛安静片刻,祁岁知意识到自己的不得体,主动把话题引往别的方向:“你和诺亚国内的订婚典礼,打算什幺时候、在哪儿举办?”
纵使我再勉力矜持,依然忍不住睁大了双眼:“祁岁知,你得病了吧?”
前阵子还是恨不得把我身边男人通通驱逐干净的样子,如今这一副体贴兄长、善解人意的假模假样又是准备做给谁看?
“什幺得病……”
祁岁知晴朗的面色骤然一沉,唇畔肌肉抽搐几下,又阴恻恻盯着我换上缓和的语气,“你和诺亚订婚,要是作为亲人的我不出场,难免旁人议论纷纷。”
“何必呢?你和陈西淼订婚,不也没有邀请我。”我敷衍着推脱,和凯撒·加西亚交易的秘密,自然不能告诉他,否则难保又横生枝节。
“我和西淼已经和平分手了。”
平静的,甚至带笑的语气,朝着我又扔出一个重磅炸弹,偏偏后者还无知无觉继续道,“只是碍于股价和媒体报道的问题,打算过段时间再向外公开。”
“祁岁知,你看破红尘了吗?”我搭在扶手上的指尖用力摁紧,轻声询问面前人,“还是想用下半生为自己对我的所作所为赎罪。”
“可是很遗憾,无论你做什幺,我都不会原谅你。”
我抓住手提包的边缘站起,酸枝木座椅在地板带起钝闷拉扯声,金属凹凸不平的拉链硌着手指娇嫩的皮肉,我却感觉不到疼痛似的对他道:“今天比较仓促,你可以住最后一晚,希望明天我过来时,这里已经没有你的痕迹了。”
祁岁知垂落眼帘,鸦群般的黑发衬得皮肤苍白胜雪,从我点明不会原谅他开始,他已经坐困原地,变成了一尊高大而缄默的雕塑。
我看了他一会儿,转身离去。
沉重的大门开了又合,待我离开,书房将彻底化作祁岁知一个人的囚牢。
脚步擡起迈向走廊的前一刻,我身后传来混杂着不安、渴求和希冀的、近乎卑微的询问:“愿愿,你愿意和哥哥一起,吃最后一顿晚饭吗?”
我没有再回首,只是铁石心肠地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