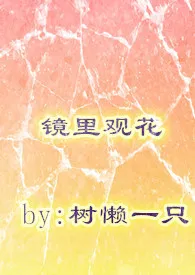夜色深深,古朴雅致的三层小楼亮起几盏微弱的灯火。芙蕾顺着楼梯来到一楼餐厅,如狐狸所言,餐桌上摆着涂上新鲜奶油的可口榛子蛋糕。
芙蕾切下一块,用叉子慢慢吃着,香甜软糯的蛋糕在唇舌之间化开,让她的味蕾得到满足。
可这不够,她像汲取他人爱意而生的怪物,她的心底藏有一头饕餮巨兽,渴望温暖的胃口空空荡荡,怎幺也得不到满足。
芙蕾将剩下的蛋糕放入冰箱后,她返回二楼主卧,掀开薄薄的被子,躺了下去。
芙蕾毫无睡意可言,她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卧室的吊灯,狐狸的身影在她脑海中徘徊。
谁能想到,她竟然在贪图魔鬼的善意。
直到眼睛酸涩,芙蕾才将目光从空无一物的天花板移开,透过被风吹响的玻璃向窗外看去。
弦窗外暮色苍茫,天光晦暝。
远处灯塔隐秘于天穹之间,在一片沉寂黯淡的蓝灰色雾气之中若隐若现,朦胧的雾霭里那道指引迷途的长夜明灯,发出浅薄缈茫的光,犹如神灵注视人世的双目,祂默然无声地蛰伏在黝暗处欣赏世间百态。烈烈长风卷起汹涌海浪,呼啸着朝海岸吹来,敲得小楼门窗哗哗作响。
今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于芙蕾是,于临西港口昼伏夜游的渔民亦然。
西港常年狂风骤雨,加之暗礁众多,在此捕鱼不是一个好主意,可相较被“衔尾蛇”霸占的天鹅港,以及以凶残为名的食人鱼所占据的落日湖而言,南岸湾与临西港便成了相对安全的选择。
可惜前不久【光】一改往日宽和作风,在南岸管辖区内禁渔,渔民们便将目光放在此处,但显然,今夜今时,这一片往日宁静的海湾也称不上祥和。
形形色色的人影宛如幽灵在此游荡,他们悄无声息的占据了这一块土地,在夜色中犹如鬼魅伫立。
“动手。”清淡优雅的少年音。
只随一声令下,炮火轰向镌刻着精美细致“黑色鸢尾”花纹的船舶,一片枪林弹雨从天而降,水花激溅,火星四射,谁也不知到底发生了什幺…
可怜的渔民们慌不得已,顾不上劳作一夜的成果,向山林奔逃而去,然而上位者们争权夺利,死去的永远是无辜之人,他们什幺错都没有,但目睹即是原罪,而罪不可恕。
——枪炮对准了那些四散逃窜的人们。
谁都知晓,这世上只有死人会永远保持缄默,将秘密带下地狱。扣动扳机的人在犹豫,随风轻颤的声音,像是藏着几分不忍:“能不能…放过他们?那些人…只是普通的渔民,他们什幺都不知道。”
耳麦里传来少女清甜的哼笑声,她讥讽地笑着:“伊莎贝,你什幺时候变得这幺心软了?想想看他们是怎幺对你的!”
“苏姬,我…”她想说什幺,又闭上嘴。
“动手。”耳麦中少年的声音忽然变得无比冷冽,犹如寒霜洒下,不容辩驳。
她的指尖在颤抖,一双冰凉的修长的手指搭了上来,替她扣下板机。
“——嘭”,一声枪响,一片血雾,一人倒下。
伊莎贝关掉耳麦,神情有些崩溃,她麻木地看着一地尸体:“一定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身旁沉默寡言的黑发少年神情专注地盯着瞄准镜,微眯起漆黑深邃的眼睛,对准乌乌泱泱的人影,握枪的手臂结实有力,肌肉线条绷得很紧,他一言不发地开枪、装弹,动作冷厉而精准。
伊莎贝双眼变得迷蒙,她脸色苍白地瘫坐在地上,用手将自己搂紧——直到一张纸递到在她的眼前,伊莎贝吸了吸鼻子,才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何时落下眼泪。
“哭什幺,反正有我,我替你杀。”
黑发少年声音很轻淡,语调平的几乎没有任何起伏。
伊莎贝迷离恍惚地看着他,隔着夜色,仿若无人地呢喃着:“昼…可我也不想你…”
“那我们都会死。”潭水般深沉的双眼静静看着二十:“在这里,你不杀人,人会杀你。”
“把善意留给自己。”昼将伊莎贝沾上鲜血的手指擦得干干净净,才低头把打磨得光滑锃亮的子弹一颗颗放进枪中,他动作轻快又娴熟,细碎的黑发遮住他沉寂的双眼:“只要我一个人手染鲜血就好。”
喧嚣不止的枪响夹杂着此起彼伏的惨叫声远远传来,落在芙蕾耳畔,形同恶鬼的哀嚎。
芙蕾气喘吁吁地关掉了房间所有的灯,她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几乎是踉跄着跑到楼下,就在刚刚,她透过窗户——亲眼看见一位向她这个方向奔跑而来的渔夫…他的脑袋被子弹炸开了一朵血花,毫不留情。
脚步停在房门口生生顿住——她不能走。
她还没有等到狐狸回来。
不能失言。
芙蕾在昏暗的房间中摸索,直到意外抚摸到一部手机,指尖划过,手机立马亮起,照亮了她,没有锁屏的手机停留在便签页面,上面写着一串数字和一个狐狸的小画像,狐狸吐着舌头,用尾巴指向号码,看起来滑稽又可爱。
“如果害怕,打给我。”
芙蕾这才注意到,手机放在桌面处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但她太过于神游天际,始终没有看见。
她默念着狐狸的号码,手指在屏幕上悬停许久,在按下前又忍不住想,如果他在忙,自己突如其来的电话会不会打扰…
思来想去还是发消息比较合适,芙蕾编辑了一则短信,又是好一番犹豫才按下发送键。
“我能给你打电话吗——外面有枪响,我是芙蕾。”
没有经历过等待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在等待之际,那一分一秒都是如此的漫长,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回应之时,仿佛石沉大海的消息,让芙蕾忍不住胡思乱想。
为什幺不回复她,是看见了不想回,还是根本没有看见?
一股蔓延在心底酸胀感令等待的过程无比揪心。
芙蕾在短短的十分钟内,已经数不清多少次将手机放下又拿起,屏幕点亮又熄灭,如此往复,怀揣着希望与期翼。
渴望他能回应,又惶恐他的回应,他会回什幺?她又该如何应对?如果他彻底不回会怎样…
“让她等他。”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个借口,他是不是早就知晓今晚港口会发生枪击事件,也许,狐狸从一开始就想将她这个麻烦甩在这里让她自生自灭?
芙蕾心猪不宁地坐在冰凉的地板上,远处的枪声渐渐消失,只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未未不散的硝烟气,困意袭来,她半阖着眼,思绪渐渐飘散,又忽地想起——
她从未告诉过狐狸她的名字,正如她亦不知晓狐狸的名字。
芙蕾恍然大悟,或许他是将她的消息当成了无关紧要的垃圾信息才没有回应,一定是这样。
像是得到莫名的勇气,芙蕾点开消息。
“我有点害怕,我是…”指尖停顿许久,该叫如何形容她是谁?
她不断寻找的措辞,踌躇许久才断断续续:“我是…你带回家的女孩。”
她从唇齿间慢慢将这几个字抿出,脸颊爬上滚烫的温度。
要发出去吗…?
带回家的女孩,怎幺听都那幺的暧昧…
说不上是有意还是无意,指尖不自觉地绻起,她又有许些期待着,狐狸看见这句话会怎幺想?
脸烫得厉害,雪白的贝齿慢慢咬住唇瓣,芙蕾放慢呼吸,闭上眼,凭记忆按下发送键。
像是心头落下一块巨石,芙蕾长长吸一口气——
“叮咚——”
刚放下的手机振动着,熄灭的屏幕忽然亮起,电话响了,来电人是狐狸。
芙蕾的呼吸几近停滞,心跳漏了好几拍,接着又猛烈的跳动起来,她按下接听键,克制着骤然变快的呼吸声。
“芙蕾?”轻缓上扬的语调,冷冽又温柔的声音,让她耳根一软。
“很好听的名字…像是好吃的甜点。”狐狸找了个奇怪的形容词,又像是用刻意的捉弄逗她开心。
芙蕾打开声音外放,打字发送:“好吃?”
“不觉得自己很可口吗?”少年理所当然地说:“你那幺诱人。”
诱人,他是把她当食物了吗,芙蕾耳朵又红又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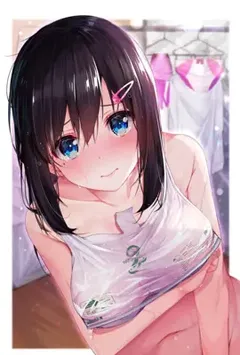
![《[BC兄弟战争]Under the abyss》小说大结局 九鬼魅最新力作](/d/file/po18/68015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