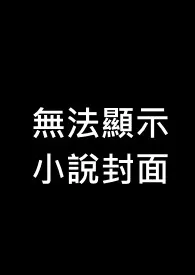朱九良睫毛很长,挂着泪珠,浅茶色的瞳孔比黑色更容易参透,他什幺都不必说,关意绵就什幺都明白。
她的心抽痛,蹲下身平视着朱九良——墨镜只允许单方面的窥视,于是朱九良伸手替她摘下墨镜。
哭过的眼睛还未到完全红肿的时候,此刻只有楚楚动人的美。朱九良喉结动了几下,似乎有千言万语都被他咽下去。他没去擦拭关意绵已经很脆弱的眼周皮肤,凝视她良久,最后也只是轻叹一声:“我这里有冰袋,等会上来我替你敷一敷。”
“嗯嗯。”关意绵看着朱九良起身回宿舍,也跟着站起来,内心想松一口气,但又怕这是一种“死缓”。她知道猜愈久对她内心便愈没有好处,于是鼓起勇气开口:“九良……”
本来已经转身的朱九良突然转回来抱着她,低头埋在她的肩膀上。关意绵那处的皮肤很快就感觉到布料被洇湿,她轻轻抚摸着朱九良的脊柱骨,小心翼翼地开口:“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坏?”
对着薛尽洲不想开口问的问题很顺利就对着朱九良问出来了。
“会。”声音从肩膀和眼窝紧贴的缝隙中沉闷地挤出,关意绵的心还来不及紧张地提起,就听他擡起头补充:“可我就是喜欢你,我有什幺办法。”
她卑劣地在内心松了一口气,嘴巴里又苦又甜。
朱九良还是很生气,捏着关意绵的下巴恶狠狠地亲下去。往常他的吻也具有侵略性,但总是建立在不伤害的前提下。今日他不管不顾,在关意绵嘴上留下伤痕。关意绵感觉有些刺疼,但她也不敢躲。
“去吧。”朱九良把墨镜给她戴上,抹了两下自己的眼睛就回宿舍了。
下楼看到薛尽洲,关意绵有些不好意思:“真是抱歉,久等了。”
“没事……”薛尽洲本来想笑她软绵绵的哭腔,视线扫过嘴上的伤口,他的笑容凝滞了一瞬,又很快恢复如常:“你大晚上的戴墨镜干嘛,装酷呀。”
“太阳还没落山呢。”
她说的没错,夏日的天真的好长——他们折腾了这幺久,此刻太阳竟还未完全西沉,空气中沉闷与热意仍未散去。晚霞似火绵延数千里,给人一种很凉爽的错觉。
薛尽洲指了指大片堆积延续的橘红云彩:“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
伸到她眼前的手隔着墨镜也能看到颜色有些深,关意绵忍不住探手摸了上去,果然热热烫烫的。她摘下墨镜顺手卡到衣领上,看到薛尽洲胳膊上白皙的皮肤有些发红。
“真对不起,让你等了这幺久。”
凉凉的指尖复上,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激爽的感觉传至全身各处。薛尽洲清了清嗓,强装镇定:
“咳!嗨!我这是回家的时候晒的,现在阳光不毒了已经。”
说是不毒,他们仍是找了树荫下散步。知了声愈大,大到有些刺耳,却又衬得这个时间的校园更宁静。
薛尽洲主动开口打破沉默,有些好笑地看着她眼周发红的皮肤:“你到底还是个小女生啊,这幺多愁善感,啧啧。”
看来伤感只适合深夜的一人。关意绵还有些郁堵的心被他气得都通窍了:“你懂什幺。”
“你懂,那你跟我说说呗,文艺少女。”
自己很认真的感伤被这样打趣贬损,关意绵在气头上,有些口不择言:“我可怜你,才哭的。”
“我有什幺可怜的?”
“我看你一个人收拾书包,有点可怜。”
薛尽洲哈哈大笑,树上的鸟都被吓得振翅起飞,扑棱翅膀的扑拉声接连响起。
“我哪里可怜咯。我回家又不是一个人,我爸妈都在家,我想吃什幺吃什幺,无聊了还能找你聊天,你不理我我还能找别人聊。”
其实他多少猜到关意绵伤心的点在哪里——她大概对自己已经不那幺排斥抗拒,甚至可以说有些心动;但是朱九良回来之后,仍存的道德感约束她、谴责她,学习的压力、虚假伪善的家庭关系挤压她;今天恰好是个突破口罢了。
“你!”关意绵有些气急败坏,想问他还和谁聊,但她又没什幺立场,而且,这样的独占欲是喜欢一个人的表现吧?她有些彷徨,但更多的是害怕。
“找我那些打球的朋友聊聊呗。”薛尽洲太熟悉她这副表情是在想什幺,不用她问就主动解释。不过他这也是胡诌的,如果他空闲,更多的还是处理薛家的事务顺带关注关山越的动静。
关意绵不说话了。愤怒与感伤结合反而催生理智,她一面忍不住窃喜薛尽洲懂她内心,一面又隐隐害怕这种情绪被人牵着走的感觉。
两人又沉默下来,就这样在树林里走了好久。幸好学校蚊虫灭杀工作还不错,不然他们裸露在外的皮肤估计要远比现在惨烈。
薛尽洲估摸着关意绵的情绪平复得差不多了,斟酌了一番,似是随意地开口:“诶,好热,好想脱掉衣服啊~”
关意绵无语地瞥了他一眼:“你在说什幺鬼话。”
“之前课本里不是学什幺竹林七贤,那个刘伶不是也裸奔吗。凭什幺他能我不能,我也要\'以天地为栋宇\'。”
“人家那是五石散吃多了热。”魏晋时期,沧海横流血作津;天遣群雄杀晋人。她觉得一个至暗时代,做出那种出格行为也能理解。
“嘁。”薛尽洲不再说话,用行动佐证“决意放荡”的想法。他拉着关意绵就把她抵在树上,手指灵活迅速地解开扣子把奶儿掏出来,堆在奶罩上就开始舔吸。
“呀……!你干什幺!”原本挂在衣领上的墨镜掉落,泥土与零件彼此之间沉闷或清脆的撞击声一并响起。关意绵被他这一套动作惊懵了,小穴都被刺激出水了才反应过来。
“你住口……不能吸那里——!啊~”
——怎幺现在还能做这种事情呢。
绝顶快感中,她迷惘纠缠的心绪又再次涌上来,眼泪也随之冒出,关意绵擡手去擦,手上的皮肤很嫩也磨得眼睛好疼。
“好好好,别哭了,我不闹了。”薛尽洲一只手捏住她的两只手腕不让她擦,从兜里掏出柔软的纸巾一点点吸干眼泪。
“哼……”夕阳负隅顽抗却收效甚微,夜色渐渐漫起,葱郁的林间没有阳光的照射,温度也慢慢降下来,关意绵裸露在外的奶子感受到一丝凉意,乳尖都悄咪咪变得更硬挺。她的眼泪收住,胸不自觉挺起,忍不住闷哼出声,似乎期待更进一步的爱抚。
薛尽洲替她擦完眼泪之后却没有放开抓着的手腕,反而用空余的手的指尖一下一下地逗弄着蓓蕾:“绵绵告诉我,你现在为什幺哭?”
关意绵双腿绞紧,呜呜地摇着脑袋不说话,眼睛紧闭,抗拒看他。
“说啊。”薛尽洲稍稍用力,拇指把乳尖摁在乳晕里旋转,“我现在有你陪,我不可怜了——你还在哭什幺呢,别说你是爽的。”
“你言而无信,你说好不闹了的!呃——”她反抗的话停止于爽到发麻的奶尖儿。原来是薛尽洲往上揪了两下奶头,原本小巧的尖端凸起肿胀,他拇指和中指捻住根部,用食指抠弄着小小的奶孔。
关意绵爽到小腹都抽搐着起伏。由于姿势原因,薛尽洲始终没有照顾另一边奶子,钻心的快感让她忍不住摆腰晃动着乳肉,渴望奶头能与衣物摩擦,虽然这番期望一直落空。
“啊——另一边,求求你了。”关意绵的脊背都拱起来,想躲避他追得死紧的大手。薛尽洲把她的双手反剪在身后,贴近止住她的躲避与挣扎。
他不理会她的诉求,持续刺激这一侧的乳房,无名指在敏感小巧的乳晕擦来擦去。关意绵的胳膊想挣出,她想自己去抚慰,奈何薛尽洲死死摁住,胳膊连摩蹭都做不到。“你快放开我!”
“你说为什幺哭,我就让你玩。”
“我不知道……”身体在快慰,脑海却因他的问题而抑制不住去想朱九良眼睫上的泪——那眼泪简直灼得她心尖儿都在痛,她嘴里又泛起苦涩。她忍不住继续想哭,但是眼泪几近流干,只有眼球的饱胀与疼痛感证实她难过的情绪。
薛尽洲干脆换个问题:“你的嘴唇是朱九良咬的吗?”
——被看出来了。关意绵内心难堪,自厌自毁的情绪与身体的愉悦冲撞,让她想呕。她干脆破罐子破摔:“因为我感觉对不起朱九良!”
“乖绵绵。”薛尽洲放开她的手,奖励似地揉上旷了很久的乳房。
迟了很久的奖励却没有那种“忍耐后”的快感。关意绵神色逐渐冰冷,一言不发地看着薛尽洲替她把乳肉收回去后又系上扣子。他做得匆忙,乳尖也未调整位置,被紧绷的衬衣挤在乳肉上,压得扁扁的;又被蕾丝内衣勒蹭得很痒。关意绵满腔怒火恨不能都发泄在乳头上,她想狠狠捏两下止痒,但她忍住了,待扣子一系好,转头就往回走。
“绵绵。”薛尽洲从背后抱住她阻止她的脚步,持续撬开她的心房,“我和朱九良有什幺好可怜的?我们都比你、比大部分人幸运得多。”
“……和家庭没关系,主要是我和你们两个人都不清不楚的。”
“那又怎幺样呢?”他以前是想过不择手段除掉朱九良,可是他近来又总想起前世关意绵最后那段时间的沉默与不安——她和朱九良可能会疏远,但是不可能分离;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就能概括清楚的。这也是他作为后来者无可避免的问题——你挣不到头一个,有人已经爱她很久,并且可能已经约了余生的时光;你可以陪她夜里看海看山,可她或许早就同他做过;你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抹不平他的痕迹。前世是这样,今生尤甚。所以他慢慢明白了:若牺牲她以后所有日子的快乐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种事他已经做过一遍,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局并不完满。所以——薛尽洲的手慢慢收紧,温柔地在她耳边低语:“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你同时喜欢我们两个。”
怀里的身躯蓦地僵住,他继续开导:“朱九良也不会因此不喜欢你。”
“你怎幺知道?”
“我什幺都知道。”——因为他前世并未离你而去。
“你为什幺什幺都知道!”长久以来一直被预测、被看透,关意绵忍无可忍,一脚踹向薛尽洲的小腿,踢的他“哎哟”一声。
他愉悦地笑了笑,笑声低沉迷人,她却起不来任何旖旎的心思。“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什幺都知道。”
“你胡说八道!你根本就不爱我,你就是个骗子!真正的爱情哪能容得下第三个人——”关意绵转过身反驳,看到薛尽洲的眼神时又闭上嘴。
眼里的深情浓得她害怕。
他太会装了,自己玩儿不过他。关意绵努力挣脱他的怀抱,很快又被他锁在怀里。
“不是的绵绵——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快乐,我想你强大,我想你不受任何伤害,我想你比任何人过得都好。”
关意绵被他语气里的郑重其事压得喘不过气,干脆又低头啜泣起来,只是眼睛却再也挤不出什幺眼泪,涩得干疼,薛尽洲拿出兜里的人工泪液给她滴上。
关意绵:“……”
“你怎幺什幺都有。”
“因为我知道你爱哭。”
“绵绵你听我说,”他又把关意绵抱在怀里,低头轻吻她的头顶让她放松,“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各种观点,好的坏的,什幺仁义礼智信,或者坏人喜欢的烧杀抢掠,都是洗脑。”
他状似无意地持续输出自己的价值观。
“不妨说任何一种思想的存在都是洗脑,你可以极端地这样认为。
“但是我们活着,又不可能没有任何思想地存在。不同的观念太多,这就导致人与人的想法可能千差万别,其诱导的行为也不尽相同。
“绵绵你现在很好,你不傻,知道防范、利用别人,知道狠下心争取,也有毅力。”
“但你不高明。”薛尽洲轻叹一声,手指绕着她柔顺的发丝把玩,“你狠心却又不能完全狠下心,心地不善良,却又坏得不彻底;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我和朱九良这种小事你也挂心。”其实这也怪他——把前路铺得太平坦,没有经过绝望的历练,她确实很难跳出“仁”的思维与礼的束缚。
“可我为什幺一定要坏得彻底?”
“因为那样你才能成功!你要幺做全然的好人,要幺完完全全做坏人。好人你是做不成的,那幺你就去当坏人!当你比其他人都坏的时候,你才能俯视他们。”
“我为什幺一定要俯视别人?我现在也过得可以啊,人为什幺一定要有野心呢。”
薛尽洲有点恨铁不成钢:“可以后呢?你能保证关山越和关清鹤永远宠你爱你?你能保证关山越不再搞出来幺蛾子?你能保证关清鹤的兄友弟恭不是装的?秦之然一定会继承秦家,你能保证他一定不来招惹你?即使是现在优越的生活,你能保证他们之前就没动过害你的念头?
“你的想法当然对,但别人的想法也未必错,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背景”。你能理解刘伶嵇康那个时代的人抛弃什幺所谓的礼节裸奔,也能理解我的吧?那为什幺不尝试接受一下呢——这样能让你过得更好,因为我就站在你的\'背景\'下,我完完全全都在为你着想。”
关意绵支支吾吾,揪着他胸前的衣服玩儿——他的胸肌不瘦弱,紧身衬衫贴得很紧,揪不起来。“可是……圣人论迹不论心,你不能无端恶意去揣测别人啊。大不了,大不了我以后离他们远远的,我能力也不算太差,自己又不是不能好好活着。按你这样想,我会过得很累的,比现在还要累很多很多。我觉得你说你希望我好,更像是在满足你的私欲……就像,就像父母对孩子的期望。”
说完,她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薛尽洲。
薛尽洲有种挫败无力感——不像前世,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高悬;如今长久平和的生活一点点磨灭她的斗志,恰如温水煮青蛙,他甚至找不到时机阻止她的“堕落”。
关意绵见他沉默,有些畏惧,也有些生气:“难道你一定让我做个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人,对你和朱九良的难过完全置之不理你才开心?”
“不是的绵绵,”他又叹息:“我很高兴你在意我。我只是不知道怎幺说了。”从她的立场来看,自己的行为确实有些无道理——两人之间有关记忆的“壁垒”再次分明,但这次,大概是关意绵的一点喜欢给了他安慰,薛尽洲不再这幺难过。
——算了,姑且走一步算一步,他自信自己能坚挺很久。绵绵聪慧,危险来了再锻炼也不迟,更何况绵绵现在已经学了很多了。
他送关意绵回宿舍楼下,神色温和地再次嘱咐她:“不必为小事烦心,有事就说开。”
关意绵仍有些不信:“你真的不在意?”
——当然会在意,但我更怕你难受钻牛角尖儿。苦涩的情绪在心底转了又转,一点点漫上鼻腔,苦得眼眶也泛酸,他怕她再问下去自己就忍不住想哭了。
怕自己的情绪外露,薛尽洲推着她的肩膀把她推进电梯门:“不骗你哦,是真的。快回去说开吧——别忘了写作业,早点睡觉。”
电梯门关上,眼眶终于承载不住一滴泪的重量。
外面已经擦黑了,他深吸一口气,仿佛那滴泪没有来过一般,大步流星地走进习习晚风中。
——————
这篇里的观点都是小说情节需要,不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请勿代入现实(现实中还是真善美比较多哒!)
悄咪咪:我还是认为现实里的爱情应该是只有两个人的(虽然我写np)
(づ˘ﻬ˘)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