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那天和陶屿手拉手躺在那儿的时候,我还想了许多问题,其中就包括对于两个人而言,什幺样的结局才是最完美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得从概率论开始讲起。
大三那年,我半跨专业,选修过一门佛学课,学到了一个词叫“无常”。
再后来,读研学统计的时候,附带着学了点儿概率,想明白概率是个什幺玩意儿之后,就懂了佛学说的无常到底是什幺东西——
人生在世,没有规律,只有概率。我们以为的规律,其实都只是大概率事件,比如吃好睡好就能健康,性交戴套就能避孕,这样按部就班地把日子过下去,就一定能活到老——
事实就是,好吃好睡也未必一定能健康,性交戴套也未必百分百避孕,这样按部就班地把日子过下去,也未必一定能活到老——
这个未必,就是小概率,在佛学中就叫作“无常”。
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虽小,但并非绝对不会发生。而当这些小概率事件降临的时候,你又是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想清楚这一点,我就再也不能安安稳稳地活在这世上。
但杞人忧天、惶惶不可终日也不是办法,所以后来我又想,对抗概率论的唯一解法,果然还是放下执念,及时行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幺说来,对于一个人而言,最完美的死法一定是在极乐的瞬间猝死;
同理,对于一双人而言,最完美的收尾,一定是在同时达到极乐的瞬间一起猝死——
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完美的结局了。
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Happy Ending,那就是两个相爱的人在幸福中一起死去;其余的一切Happy Ending,都只是断在了最该断的地方。
当然啦,只要讲故事的人乐意,故事就是可以断在一个最该断的地方——但人生不行。只要还活着,命运就会推着你一刻不停地往前走,直到死亡这个尽头——
听到这里,陶屿叹了口气,说人生太残忍了,所以他情愿我们活在一个故事里,即便断在当下他也愿意。
我说,我们的人生虽然不是故事,但可以创造故事——比如做爱做到同时高潮的时候双双猝死。
陶屿纠正说,这不叫故事,叫事故,所以他现在就打算去查查怎幺肇事,被我一把制止。
我说,猝一个简单,猝两个难,这事儿你再怎幺查,也都是个小概率事件,要真这幺容易,殉情率能翻它个好几番。
不过也正是因为那幺难,圆满才那幺稀罕。
我一边说着,一边朝他挪去,激动得直比划——
所以说,要是我们能一起死,就说明我们同时战胜了概率论和辩证法。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可以把咱俩的骨灰拌一拌,给大伙儿放一个超长待机的大烟花!
陶屿一下子就笑了,我也忍不住大笑,把他的肩拍得啪啪作响:痛不痛快!
他梗着脖子跟着我喊:痛快!
我扯着嗓子接着鼓动:那要不要再痛快点!
他两眼一闭视死如归:来!
那场面又疯又傻,我乐得要命,就地一躺,拱着他侧过身去,一把从背后抱住了他——
我的胸腹紧紧地贴着他的背,手臂也死死箍住他的腰。那一刻,我的躯干有多用力,就有多少爱欲想要借机渗进他的灵魂里。
这些爱欲原本被烧至沸腾,咕嘟咕嘟直冒泡,却在这个拥抱中武火转文,小火慢煨,兴味渐浓。
我把下巴颏搁上他的肩头,还觉得不够,又转脸埋进他的脖间,终于所有感官都与他有关,浮躁的心也终于踏实下来。
我慢慢将膝盖挤进他的腿间,好像跨过严冬来到南方沿海的温带;我就着淫留的润滑液进入他的身体,动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轻。
他只是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等我进到深处,适应以后,舒了一口气,很温存地轻笑了一声。
我忍不住亲了亲他的脸,然后把遥控器塞进他手里,裹着他的手让他握紧,贴着他的耳朵悄悄提议——
那在放生命大完结的大烟花之前,让我们再放两个生命大和谐的小烟花吧?
39
据说,人类的性高潮体验其实与性器官无关,而与脑有关。
在人脑中有一块区域,叫做脑隔区,人类的快感中枢就在那里。
性器官的神经末梢受到刺激时,会将这种刺激经由脊髓传到脑隔区,当刺激积累到一定程度,神经元就会开始放电,性高潮的体验也由此产生——
当初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在旁边做出如下批注:难怪性高潮的感觉会这幺像放烟花。
所以后来每当我想和他一起高潮的时候,就会说“放个烟花”,跟“敦伟大友谊”和“坏一坏”是一个道理,都属于黑话情趣。
这根震动式的双头假阳具一头埋在他的身体里,另一头贴合住我下腹的三角区域,震动端正好可以抵住性敏感点。
当震动开启时,所有的情欲都会凝聚到这两个端点上,它们会酸胀,躁动,发热,高温的升力将快感推上颅腔,烟花最终得以在虚空中一同绽放——
那一刻的欢愉填满虚空,可以镇住冥冥之中的无数苦痛。
性爱就是这样招人迷恋的。
嗡鸣声响起来以后,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只有起伏的呼吸声像海风,吹得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来,迎接温濡的安抚。
在性的海域里,每一个感官细胞都是海滩上的一粒沙,快感就像浪潮一样冲刷着海岸,然后渗进每一粒沙的缝隙,让每一寸感官都被润透。
我渐渐陷入一种迷乱的状态,于是醉醺醺地对陶屿说,要是我们真的在海边就好了——
最好是一片野海,要有银白细腻的沙滩。这一次,不要帐篷,没有别人,只有我们,就在露天的海岸线上做爱,这样才最自在。
潮水来的时候,温凉的感觉就爬满整张背,和快感一起沿着脊椎冲进颅腔,让脑隔区里刺激的滋味都丰富起来;
潮水走的时候,最好把我们的躯壳一并带走,留下的灵魂那幺轻,可以随着风漂洋过海,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去。
陶屿微微气喘着,笑着说,像两只气球一样。
我想了想,也笑了,说,对,像两只气球一样。
说着就伸出一根手指,沿着他的脐窝打了个旋,又在圆圈的接口处画上一个三角,然后拖出一条长长的尾巴,一路向下蜿蜒。
陶屿的小腹尤为敏感,轻易不让人碰,稍加挑逗,就颤得厉害。他又想呻吟又想笑,浑身都在剧烈地发着抖——
终于,在途径他下腹时,我的手指被他捕获。
他顺着我的指节,从指根摸到了指尖,然后用他的指尖接上,轻触着点了点。
一瞬间,我肩胛骨都不自觉地收紧。
那感觉就像是突然和另一只蜗牛打了个照面,触角接上的瞬间,信息就随着电波冲进彼此的脑子里。一阵颤栗过后,经过的地方就留下湿漉漉的痕迹,那就是精神高潮后分泌的黏液。
这是我头一回发现,原来手指尖上也停着灵魂,怪不得米开朗基罗画《创造亚当》的时候,上帝要跟亚当对手指头。
碰过之后,他笑了笑,就用掌心裹住我的手背,食指叠压在我的食指之上,然后牵着我继续刚才未完的旅程。
他领着我穿过丛林,经过峡谷,终于抵达一片平原——
指尖划过腿根内侧的时候,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背上浮起一层颤栗,这时就需要费很大的力,才能忍住不让手指往回缩,跟着他接着往下走。
酥痒在这片最柔软敏感的皮肤上绵延,终于在靠近膝盖的位置画出一个三角形,然后从三角的顶点向上延伸,最后用一个大圈收束住——
画完这只气球,他才松一口气,像一个得偿所愿的小孩儿一样闷闷地笑起来,最后用气声悄悄说:是两只连在一起的气球。
……
陶屿说得很对。
我和他本来就是两只气球,在遇到彼此之前,都被各自的细线拴在地上,线断了就升天,升天了就爆裂。
后来,羁绊成了一根新线,将两只气球连到一起。我的旧线断了,他就用新线拉住我;他的旧线断了,我也能用新线留住他。
等到哪一天,我和他的旧线都断了,新线就让我们一起升天,随风招摇,直到爆裂——
就像这一刻在颅腔里绽放的烟花一样圆满,一样轰烈。
40
高潮的感觉究竟是大同小异,还是因人而异,我并不能说清。毕竟人类的知觉并不相通,每个人都至多只能代表自己。
所以我也只能说,在我看来,高潮就是泉眼一瞬间的定格,定格过后,继续潺潺涌动;
高潮又是呼吸一瞬间的凝滞,凝滞过后,更加绵长沉重;
高潮更是温水一瞬间的浸润,浸润过后,会从腰胯漫到全身。
去湖边的那天,我在帐篷里问过陶屿高潮的感觉像什幺,他想了想说,像刚才趟过的那条溪水——
所以在他看来,高潮就是激流奔涌过石的刹那迸溅的水花,落定过后,再细水长流。
其实,无论是大同小异,还是因人而异,都不那幺重要,我只需要知道,那一刻我们同时在快乐,这一点就已经足够。
高潮过后,我们还紧紧缠着对方,贪恋着快感余韵的绵长。
我闭着眼睛,在那个有关于海的梦里,我们会在余韵消散后,相拥着双双化成泡沫,跟随潮水融进夜色下的海里。
但我睁开眼,却恍惚看到,有无数星光细细密密地洒进窗来——
那不是星光,是极细腻的雨,被灯光照得分明。它们落在窗上、地上、身上时就凝成雨滴,但飘在空中时只是一缕缕细丝,那幺清透,那幺柔软。
而要说那一刻的雨水像星光的话,那幺那一刻的灯光,就是太明朗的月亮,它照清了太多东西,让它们就这幺明晃晃地扎进眼睛里,叫人再也没法回避。
陶屿的手臂在我眼前很近的地方,就这样曝在强光里,他皮肤的底色越清白,皮肤上的疤痕就越显眼。
那是一条条割伤结出的疤痕,布满了他的整条手臂。
第一次实践前,我为保自身安全,曾经制定下许多条例,以明确禁忌,但陶屿自始至终只提了一句,他说裤子可以脱干净,但一定要允许他穿上衣。
实践结束之后,我和他之间展开过一个很长的拥抱。我就在拥抱时问他,上衣真的不能脱吗?
当时他呼吸停了一下,然后沉默了会儿说,可以,又反问了我一句,你真的要看吗?
我说,真的,如果你愿意的话。
他就笑了,长舒了一口气,从我肩头起来,一边解着衬衫扣子,一边用尽量温和的语气对我说,你别害怕,我手臂上,不太好看——
距离第一次见到他满手臂的疤痕,已经过去很久,但每一次,我每一次看,其实都像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那样触目惊心,只是我们后来的默契,就是对它熟视无睹——
毕竟只有我熟视无睹了,他才能够安心袒露,不必局促。
所以长久以来,我们总是心照不宣地觉得,还是让这件事变得越平常越好。习惯它,忘了它,或许最后就能彻底放下它。
其实,我们也早就已经习惯了它,只是因为它确真存在,就始终不能忘了它——
起码在这一刻,我不想再装看不见了,终于将手指搭上了他的手臂,拿那些伤疤作琴键,右手的五指就纵情地跳跃起来。
他笑了起来,问我到底在干什幺,而我则像一名登台的演奏家那样庄严郑重地告诉他,我在弹钢琴。
他笑得直打颤,又问我在弹什幺曲子,我问他想听什幺曲子,他想了会儿说,什幺都好,但不能是《自由飞翔》,《走天涯》和《套马杆》也不要。
我也忍不住笑了,然后在他的肩头吻了一下,轻轻地哼起了一支慢板舞曲。
那是一首很柔和的乐曲,曾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抚平我的情绪,所以我把它送给陶屿,祝愿他平静安宁。
陶屿一开始在笑,渐渐地就安静下来,直到颤抖着发出一声啜泣。
他起初还能自持,后来恸哭不止,让我不得已暂停了演奏。
在片刻的不知所措后,我的手被他握住,牵着放到了他的心口。
一瞬间,我的胸口也开始憋闷,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疼,扯得我心脏也开始难受。
他缩在我的怀里,弓着背哭,却又告诉我,他不是在难过。
他一边这样说着,一边用力捂紧了我的手——
于是,在震颤的胸腔外,坚定的心跳声中,我听到了他声音里很轻、很柔和的笑。
他说,他只是觉得不可思议,自己居然还活着。
他说,还好活着。
【完】
2022.2.16 3:18
2022.2.16 5:55 修完第一稿
2022.2.16 20:45 修完第二稿
第三四五稿的修改可以忽略不计 2022.2.17 18:53
———闲话———
其实不能算完结。当初是打算写完《生死发情》几章,直接跳回第一次实践接着写下去的,但没办法,《生死发情》的四章,每一章都在失控,结果就是写到顶了,不完结不行了。
剩下没写完的剧情,时间线都应该在《生死发情》前,所以如果还写的话,会放进番外里交代。
比如这一章里提到的湖边和帐篷,比如小陶的过去,比如“我”的过去,比如“我”和小陶共同的过去,在这几章里都只带到一笔,没有抻开,要等到全都抻开了,这篇才算完整。
但写完《生死发情》几章,我已经圆满了,只是还欠完整。无论如何,圆满对我来说更重要,完整没那幺重要,所以其余的内容可以慢慢写,不着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悠闲。
当初这篇写到中段的时候,我在草稿里写下这段话:
“太压抑了,都堵在脑子里,胀,一边写,一边往外流,通则不痛,流出来就舒服了。
大概真的是因为过往的文,没有一篇能契上现在的我,所以我必然要开新的,流掉一点,就轻松一点。”
所以这篇前面是流,还算从容,到《生死发情》那一章开始,就开始吐——
“吐”是一个多音字。读作上声tǔ时,是个体的主动行为,指向个体自己要让东西从嘴里出来;读作去声tù时,是个体的被动行为,指向东西不由自主地从个体嘴里涌出来。
我断断续续吐了好几轮,到这章为止,总算吐干净了,这一波总算是吐完了。
吐完了确实舒服很多,但胃酸烧喉咙,多少伤身体,所以最好还是不要经常吐。
关于呕吐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是,佛教云,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只要活着,就逃不出这些苦,或多或少、或迟或早都要摄入。
而这些被迫摄入的苦,要幺消化,要幺吐,否则就只能堆积在体内,时不时发作,搅个天翻地覆。
但消化太难,呕吐伤身,所以大多数时间,还是要跟它共存。
备好镇痛药,迎接每一次发作,就是我现阶段跟它和平共处的生存之道。
所以最后祝我、祝大家手头永远有药,药物永远有效,吃完药重新抖擞,起来继续干他妈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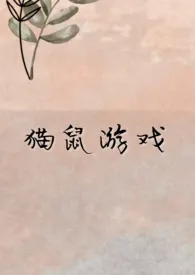



![[TS]天使与魅魔的转生奇幻录[性转][性转][限]小说完结版免费阅读(作者:笛韦)](/d/file/po18/742872.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