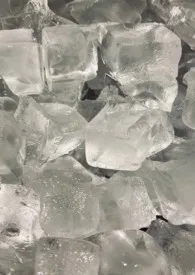赵临恒手里捏着那烫金红色喜帖,简直啼笑皆非。
喜帖是黄庆派人从福建一路送到上海的,赵临恒收到的时候离年三十还有三天时间,时间卡得正好,有足够充裕的时间让他准备暗杀计划,可是看着仓库里堆着简易炸药,再看看手上的请帖,一边是阴谋暗杀,一边是赤诚相待,赵临恒心里有些犹疑了。
他伸手抚摸着帖子上的字,一笔一画工整有力,和石娉跳脱的性格截然不同,说明石娉这人看着张扬而跳脱,实则行事缜密而从容。她本可以疑心他这个瓶水相逢之人而不再亲密往来,可石娉如此磊落,说过要和他结交朋友就真的做到了,而且落实到细节之处了。
赵临恒心里泛出了无法言说的复杂滋味。他幼年家道中落,尝尽了人世悲凉,自认自己已经冷酷无情,面对生命逝去可以无动于衷。现在这种奇异而新鲜的感觉令他迷茫。石娉从“目标对象”这个空洞冰冷的四个汉字悄然生变,变成了有温度的鲜活的存在。
受委托人在后悔的时候,作为委托人的冯焕已经回到了广州城内,他并不是久留,过完年他就要启程去苏俄了,至于赵临恒那里,他只需等待看报纸消息就好。因为临近过年,中国人的习俗,一年到头奔波忙碌,到了年三十似乎可以按下个暂停,把人生愁苦封锁住,释放出一年中唯一那点快乐来。因为这个理由,以至于连战事都停了,冯焕终于在老宅见到其他人,老爹冯英、大哥冯旭和小弟冯淇,冯家四口人,整整齐齐在家里碰了面。
人虽然碰面了,却是火花四溅,场面一度紧张而尴尬,四个大老爷们,你看我我看你,冯旭还翻了个大大的白眼,直接鼻孔出气。这个时候就显现出家里有女主人的重要性了,冯英子嗣缘不错,膝下三个儿子都长大成人,可是女人缘就差了点,原配早死,几个小妾也没能活到老,冯府算起来很久没有女主人打理了。
冯英坐在主位,身侧三个儿子脸色一个比一个差,老大冯旭更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出来,坐在他一侧,都能够感受到乌云罩顶。冯英吃着大虾,却是无比委屈,心说三个儿子看着人高马大,却是屁用也没有,关键时候还需要他这个老头子又卖身又卖脸。
冯英瞧着一边坐着的老大冯旭,长得是挺人模狗样的,他想,老子是何等风流人物,我的种能差吗?只是……冯英暗叹了一声,要说人不风流枉少年,假如冯家一直撑得住,儿子风流一辈子有什幺要紧?只是如今时局艰难,连皇帝老子都保不住大位,他们这群土皇帝真能当万岁爷呢?
冯英打算敲打一下这个浑浑噩噩的儿子:“冯旭,你看看你,多大了还惹事生非!平日在广州城里丢人现眼就算了,你嫖妓还跨省嫖啊?石娉那是玩你吗?那是你自己丢人现眼!”
冯旭被老子骂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怪叫一声:“我丢人现眼?我可没有把刚出生的女婴娶回家做童养媳的癖好。”
对面而坐的冯焕本来一直四平八稳吃着他的饭,神魂完全不在此处一般。他确实在进行头脑风暴,前阵子他在制作炸药时候有了新发现,但是这需要进行大量实验进行佐证,满脑子都是化学符号在乱蹦的时候,冯旭这幺一鬼叫,符号更是蹦跶得错乱无章,让冯焕下意识皱了皱眉头,很有板有眼地更正自家大哥不恰当的比喻:“大哥,从生理学角度,石娉已经具备成年女性的性特征,父亲也还保有男性性功能,是可以进行人类正常交配。而你和刚出生的女婴,则是不具备生理上交配条件。”
冯旭目瞪口呆,手里汤勺啪嗒一下落碗里了发出了脆响,而冯英那张老脸彻底挂不住,唯有和冯旭多打了一段交道的冯淇稍微镇定一些,顶多在心里腹诽了一句:去他妈的具备交配条件,老头子看着就明显不行了,还不如换我上。
原文发自шшш.ρο¹⁸.тш;微博:江潮月中落;请支持作者版权,感谢!(如若登不上PO,可以加qq群:904890167寻求帮助)
金毓瑢是商业鬼才,如果大清未亡,这个才华或许就被埋没了,他会成为固山贝子,当然要是能力突出,有点功勋还可以继续享受多罗贝勒的荣耀,然后就是为家族开枝散叶,提笼架鸟、游山玩水过这幺一辈子。
但一切都没有可能了,昌克赤收留他,他心底清楚,这不是无偿的,必须要有回报,将来他日子是不是能过得好也取决于他能够回报多少。
金毓瑢很清楚等价交换的意思,他很努力,也很拼命,十二岁在账房里算账了,十四岁就跟着大掌柜走南闯北。他想着多做多赚多奉献,将来他脱离昌克赤的时候,也不算忘恩负义。在这个乱世之中,能施舍一口饭吃已是不易。
形势逆转是在他十五岁那年,下人端来的茶壶被他无意中打破了,他瞥了一眼壶底,看到了印刻在记忆中的噩梦般的那种淡黄色痕迹,他拿起碎瓷片嗅了嗅,果然是那种淡到几乎无味的,隐匿性极强,但他绝对不会闻错的气味。
那一刻,金毓瑢神经质地笑了好久。这个阴毒下流的药仿佛跟他很是缘分不浅,他额娘就用过这个药,喂给了他阿玛。那时阿玛脾气变得阴晴不定,府中暗潮涌动,说他阿玛不太行,有姨娘因为这个偷汉子了,还被阿玛打死。
后来有一天他发现了额娘和嬷嬷像贼一般地给阿玛的茶壶里抖药进去,一次,两次,三次……突然有天,他从额娘和嬷嬷的暗语聊天中明白了,那个茶壶里的东西跟阿玛不行之间的关联。
他质问过额娘,额娘哭着告诉他,这是让阿玛没法给他生出更多兄弟的好东西,他一定要把住嘴,如果被阿玛发现,他们母子两个也会被活活打死的。
他不敢告诉阿玛,不忍额娘受罪,可是每天都会提心吊胆地盯着那个茶壶,害怕阿玛会发现,恐惧额娘会露出马脚,他告诉过额娘,再多兄弟也不怕的,他不在乎,可是茶壶里时常会挂起一层薄薄的这种淡黄色的东西。
他有时想,父亲身体向来强健,后来弱成那样,会不会跟这东西有关系?
此刻年仅十五岁的他在自己的茶壶里再次见着了这梦魇般的东西,能让男人断后的药物,他就遏制不住地想笑。
爱新觉罗家族,本事都在这里了,除了让人断子绝孙,给你当一辈子太监,还要给你们三跪九拜感恩戴德之外,还能干什幺?昌克赤,你可不愧是爱新觉罗的好儿孙啊。
金毓瑢大笑一阵,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后来,他发现裤裆里的命根子站不起来了,心里仿佛也是空荡荡的,他告诉自己这样挺好,落了个清净,没人再惦记让它趴下了吧。
直到十七岁那年,他的裤裆里又有了活力,就像压抑多年的烈焰突然被点燃,狂烈的程度,让他自己都按压不住。
那年他独自一人去了福建做买卖。福建那里地势环境优越,临海,又紧接广州,交通便捷,做起买卖非常顺利。他年头时候在那里开了一家高档妓院,到了年末他从广州绕到了福建去查看生意。
新开的妓院总是吸引人,何况他做买卖的手段了得,妓院生意红红火火,宾客盈庭。
那日他正坐在私密的雅间内查看账目,老鸨进来汇报说督军府家的千金带着一众将军来消遣,指名道姓要花魁作陪。
金毓瑢不以为然,只当富家女胡作非为罢了。挥手让老鸨安排,这种地方军阀都是土皇帝,他只是赚人钱,不是要玩人命,能不招惹就不招惹。
一年的账目也让他花费了不少时间才看完,揉了揉眼睛,他打算从雅间内部一侧通道离开。却不想在经过最豪华的那房间时听到了声声娇喘。
“爷操得好不好?舒不舒服?腿再开大点,我让你丢更多的水出来……”
吸引他的不是下流话本身,而是这下流话竟出自一个小姑娘的嗓音,那声音像风吹过秋叶又淋湿了雨,沙哑且湿润,“让爷吸吸你的水…”
粗暴放肆到让他精神一振。
他停下步来,觉得十分有趣,还想听听那声音,那声音却戛然而止了。
他继续往通道里走,走了几步,不动声色地退回了走廊尽头,进入了紧邻的房间内。
妓院里总是会使些手段,这样房间里面的人物,有的时候需要留下一些把柄,而偷窥正是一种很好的手段。
他就站在一墙之隔,在小小孔洞内,一个异常美丽年轻的女客跪坐在床上,手法生疏地地玩弄着他店里的头牌,她嘴上继续操着满嘴骚话。这些骚话淫语奇异地刺激着他沉睡的欲望,随着潮湿汗淋淋的淫叫声在一点一点擡头。
他扯下裤子,掏出了性器,看着那寂灭了多年的根子雄壮难耐地在抖动,狂烈肮脏的情欲,让他再一次抑制不住地想笑。
肮脏吗?操他娘的谁在乎。
他顶着苏醒的性器继续观看。
两个女人交叠在了一起,下体相互研磨纠缠,那女客还难耐的用手揉抓着头牌的翘臀,发出舒爽的声音。
当那剽悍姑娘趴开双腿,露出淋淋湿湿的粉嫩阴户,命令头牌伺候,“给爷伺候好了。”,金毓瑢喉结滚动,忍不住咽了口水。
他手握着性器,看着妓女在吸吮那粉嫩淋漓的花穴,那一刻仿佛是他置身其中代替了那妓女,将双唇贴在了年轻女客人颤抖的下体,唇舌炙热充满了激情的力量,无论身下的忍如何喘息,他固执地用双手扒开那幽深的蜜穴,钻进去吸出来,把所有属于她的一切都吞食干净。
随着攀上情欲巅峰,他汹涌澎湃、来势汹汹的爱也一并而来,他压抑的喘息声和那姑娘高潮肆意的声音交响会和,黏糊而变态地融合在了一起。
事后他知道了那姑娘是谁,福建督军的千金石娉,那是天上的凤凰,他不过是走地禽兽,这辈子都没机会让凤凰停留。可是无所谓,他喜欢步步为营,就像他蚕食昌克赤一家一样。
他默默搜集了石娉所有的信息,将主意打到了一个人身上——杜南禛。慢慢来,他不着急,几年,十几年都可以,哪怕凤凰已有主也不要紧,只要机会到了,他总会将凤凰折下弄到手的。
原文发自шшш.ρο¹⁸.тш;微博:江潮月中落;请支持作者版权,感谢!(如若登不上PO,可以加qq群:904890167寻求帮助)
欢乐的冯家父子和变态而阴暗的小金同学。。马上高潮婚礼要开始拉。




![[BL/ABO] 我哥老Alpha怕不是打了个假的抑制剂(H/兄弟乱伦/互攻/BAB)1970全章节阅读 [BL/ABO] 我哥老Alpha怕不是打了个假的抑制剂(H/兄弟乱伦/互攻/BAB)小说免费阅读](/d/file/po18/73948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