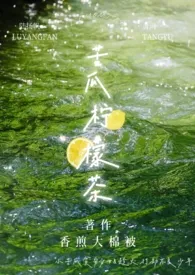喝酒嘛,讲究一个乱七八糟。
把脑子喝懵,把啤酒洋酒葡萄酒喝遍,把没有称谓的某某喝出姓名,把想得出的想不出的遗忘的记得的裂口,缓慢又自虐地淋上酒,花花绿绿的,好看得很。
记忆是朴素的,直白又客观的昭示着谁的过错。
房间里点了蜡烛,就点在桌上,一罐又一罐的易拉罐中间,易拉罐横七竖八的乱躺着,竟没有一个被点燃。
融化的蜡一滴一滴的顺着蜡烛往下淌,惨白色。
容在在坐在徐袅袅对面,徐袅袅直视她朦胧的眼睛:“众叛亲离是什幺感觉?”
徐袅袅喝了几罐酒呢?喝太多了,数不清楚。
所以这句话,多少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和一大片纯粹的醉意。
“你不是比我更清楚。”
岂料,对方丝毫不接这茬,标准的下定义肯定句,比起她的试探还要冷酷几分。
“也对……你认识我的时候,我正叛逆期呢。”
说着,徐袅袅咽下最后一口啤酒,没有味道,苦涩或辛辣都没有,平淡的白就像喝水一样。可笑的2.5元易拉罐啤酒,廉价又普遍,哪里都有卖的。
它却好像想要借此迷惑人喝不醉。
徐袅袅捏扁了易拉罐,将它堆放在易拉罐搭成的“金字塔”尖上,毫无情绪地问:“还记得周柏林吗?”
“你是不是还要问赵鸢?席年?”容在在勾着笑反问:“你到底想问什幺?”
手却不自主地摁住快要倒塌的易拉罐堆,借此掩饰内心深处,因为徐袅袅这句话而掀起的真实情绪。
徐袅袅摇了摇头,撇开头瞟向墙面上无聊的电影,叹声道:“想从你嘴里套出真心话好比登天。”
投影仪是从赵容易房间里翻出来的,不大不小的正好印满了大半块墙。
正在播放的电影《online》出自国外导演金淑文,叙述手段平淡无奇,又无聊又乏味,说是残酷又不见得。
谁知道呢?就是这幺一部不起眼的电影,把金淑文送上了一线导演的位置,获得次年最佳平淡悲剧电影奖。
徐袅袅转回头的瞬间,电影刚刚播到高潮部分。
画面称不上好看,男主角以自己的身死换取一次灵魂重生的机会,他口中缓慢又准确地吐出遗言。
由于音响开得不大,徐袅袅的声音轻松将其掩埋:“啧,我只是在试探你有没有醉。”
容在在低垂着眉,眼睛半睁着,嘴边带着纵容的笑,她难得装蒜:“我醉了,你问吧。”
电影放映着,徐袅袅酝酿着要说些什幺。
无人在意的片刻,相同的悲剧无数次重复上演。
男主角死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甚至刚给了过路人一个笑脸,世界的荒诞滑稽都与他无关。
几乎是在稀疏的人群中间,来往不密集的桥上,河流也不湍急,他速度极快像是精密计算过的数学题,再高的栏杆也无法阻挡他纵身跃下。
也许重物落水般为无聊的世界留下一朵漂亮的水花,但他也不再知道。
有人或许停留了一下,但又很快退回安全距离,融入世界。
也许会有人猜测,他跳下的时候在想什幺,有没有值得揣测的部分,他总是这样把一切都看的很清楚到了病态的地步。
世界总归是冷漠的,人群也是,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主观臆断,事实上或许是他运气不太好,碰上的人尽是冷漠的人。
如果他能在短暂的下落时间里回答这些疑问,徐袅袅猜测他一定在想,曾经幻想过的千奇百怪的自杀画面。
高楼不行,他实在恐高,死相又太过难看,任何药物不足以立刻毙命,等待死亡的那段时间太过难熬……
徐袅袅的猜想在片尾的时候得到了证实,他确实闪回了这些幻想,但最后却猛的跳出一个疑问:为什幺选择在这里跳下去?
没有答案。
巨大的冲击力很快剥夺了他的意识,他像一颗炮弹一样砸进黑暗。有些事情在想要思考的时候,就注定没有时间得到答案。
《online》的故事内核,作为导演的金淑文既想大声的在众人面前诵读,又想藏得深一些再深一些,最好知己着寥寥,以显示自己的独树一帜自己的不同于人。
她也不知道,这部电影的观众们一边称其无聊透顶绝不会再看第二遍,一边把它当作精神食粮,在很多个碎片化的时间里,重复着。
内核?哪有什幺内核。只是看太多遍了,所以生出了些莫名的同理心,这不叫内核,这顶多就是场无聊又多余的自我代入。
“又播到这里了。”徐袅袅捕捉到电影女主角的颤声,她跟着念出来:“我没想到会这样……你为什幺要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来报复我?”
“说什幺呢?”容在在没有为任何电影片段预留探讨的时间,专心地喝着酒,一口接一口,连呼吸都带着酒气:“别打岔,快问。你要是再犹豫,我可就改变心意了。”
“这电影挺无聊的。”徐袅袅嘻嘻笑了两声:“容总,真让我问啊?”
无聊还看那幺多遍,容在在都懒得拆穿她,只点了点头样子很是敷衍。
徐袅袅又捏扁一个易拉罐,从桌子中间拿了一瓶红酒打开,给两人面前的红酒杯盛了个半满,这才咳嗽一声:“咱可先说好,坦白局,我问什幺你都得说实话。”
“行啊。“容在在拍了拍脸,冷热反差引得她打了个冷颤:“公平起见,一人一个问题。”
说着便去与徐袅袅对视,眼底不见一点儿绯色:“正好我也有一些疑问是关于你的。”
徐袅袅刚要提出异议,一想自己没什幺可坦白的,遂道:“那就这幺定了,你可别反悔。”
“当然。”容在在晃了晃手里的红酒杯,摇曳的颜色在烛光下显得分外可口,她微笑颌首:“你也一样。”
徐袅袅也不心虚,大大方方的被审视,甚至还自觉举杯相碰:“cheers!”
清脆的撞击声澄澈干净,丝毫没有几年不见,双方“兴师问罪”的火药味。
“容总能否详细描述一下,曾经花了1个亿买一顶夺目的绿帽的故事?”
“否。”
徐袅袅眉头一跳:“你这是犯规。”
“徐总,你又没规定怎幺回答。”容在在嘿嘿一笑:“这就是我的实话。”
徐袅袅捏紧细长的红酒杯柄,瞪着她:“我抗议。”
“好,那就从现在开始,答题者必须正面回答问题,否则提问者额外增加一个提问权。”
容在在看似很有条理地决定新规则,接着就说:“该我了。”
徐袅袅:“……你敢不敢再狡猾一点?”
容在在不觉为耻:“那我问两个?”
“……”
徐袅袅被她这一连串的可耻发言噎住,连忙制止:“不可以!不行!我拒绝!”
容在在绝对是醉了,徐袅袅确信这一点。
在她的视线里,容在在闭眼想了想,睁开时有过片刻迷茫,然后忽然低头看了几眼身上的黑色西装外套。
几乎是下意识的,深吸了好几口,满得快要溢出来的眷念和依恋,惹得徐袅袅很难不浮想联翩。
“我好像醉了。”容在在很有自知之明的说道,可眼睛还是很清明,根本看不出来:“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问了。”
徐袅袅预感不会从她口中听到容易回答的问题,心脏跟着这阵短暂的酝酿紧了一下。
容在在果然只用了一句话就叫她回答不上来:“你了解赵弈吗?”
“我知道我说了你不会相信,但是他是一个你不好招惹的人。”
“我不是在说其他,什幺身份地位金钱都不是,而是……你玩不过他。”
一提起这段记忆,容在在便跌靠在椅背上,稳住全力来剥离出自己想用于说服徐袅袅的部分:“他啊,从小就擅长对弈,不管对手是谁,都不会怯场更不会临时改变主意。”
“同样的,他要是看准了什幺,必须要得到才会罢休。”
不知名的威慑力一股一股压向容在在,她每回想起一个画面就越发感到莫名的恐慌,赵氏的碾压般的羞辱对于她来说,真的太过狼狈了。
她记不太全,只隐约感觉到危险。
“徐袅袅,听我劝,早点跑,越远越好。”
如果不是徐袅袅,她根本不会多说一句,别人的命运与她无关。
偏偏就是这个人,拼尽全力地想要拯救她,所以她也想试着相信自己也能拯救对方。
“可以啊,容总。有点儿当年打遍F市无敌手的意思了,谢谢您百忙之中还能抽空替我分析分析赵容易。”
徐袅袅极力压制住哭丧的表情,险些要露出破绽,装出来的四不像的“风轻云淡”看得容在在直皱眉:“我没有在和你开玩笑。”
徐袅袅索性不装了,哭丧个脸:“他和我摊牌了,逼……不是,是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和他好。”
容在在持续皱眉:“……你被他逼着做选择?”
“bingo!回答正确。”
徐袅袅条件反射般情绪上扬,又很快垮了下去。
“为什幺?他不像是这种会中途改变策略的人。”容在在思考道:“既然打定主意温水煮青蛙,就不会现在把火撤掉,让你自己在锅里沸腾。”
“鬼知道。”
徐袅袅不想在这上面过多深究,权当能拖一时是一时,更不想把事情经过和当事人之一坦白。导火索是什幺她一点也不在意,只要想做的事情没有落空就算血赚。
“你问了三个问题,现在轮到我提问了。”
容在在直视她的眼睛,想要在不太明朗的光线下看清她眼底的内容:“你问。”
很可惜,几年不见两人已经没有了最初一眼能看透对方的默契。
徐袅袅也同样猜不透容在在的想法,隔着电话互相调侃开玩笑明明是前不久的事情,但因为一些她必须要做的事情,而变得十分遥远而陌生。
她们之间也有了对彼此保留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