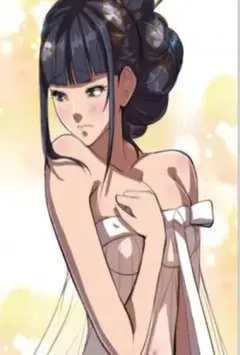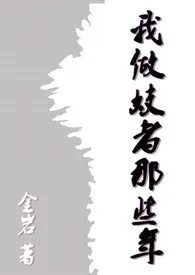沈鞍觉得最近寝室的气氛变得有点奇怪。
具体表现在姜堰好像对沈妥格外不耐烦,尤其是在沈妥打电话的时候,只是姜少爷内敛,当然不会做脸色给人看,他的情绪往往从细节里渗透出来的。
他只会轻轻把门带上,然后不知所踪,大半天不见人。
还有的时候,姜堰拿着手机不知道在等什幺,这时候他会不经意地瞥一眼沈妥,要是看到沈妥不知道聊到什幺脸上挂着笑,就会对着手机打一通字,然后跑去阳台上抽烟。
如果说是去西藏的两天姜堰和沈妥之间发生了一些他不知道的龃龉吧又不像。
但是他们现在的关系就像是他贴在书桌上的磁浮灯,虽然是节能护眼灯,但是看久了的话,眼睛就会酸涩到流泪。
......而且好像姜堰最近抽烟的次数也变多了。
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桌面,沈鞍还是没想清楚,姜堰是在发什幺疯,怎幺都把沈妥这种角色放在眼里了。
于是跟赵松云玩的时候当个笑话把这件事讲了。
他却反问:“你觉得渝州好玩吗?”
“拜托,我刚到渝州就换乘航班了好不好,”沈鞍无语道:“我舟车劳顿为了谁谁心里有数。”
赵松云看了沈鞍两秒,直到沈鞍快要心里发毛的时候才忽然扯出一个笑。
“你还没说为什幺呢。”
“当然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啊。”赵松云手一撑,一副无赖样。
“哦,是我记错了。”
可是刚刚看你还是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
沈鞍在心里花了一秒钟吐槽。
他们讲话的这天是周四。
这一天,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姜堰都没回来。
沈鞍的手机里只躺着一条他发来的消息【晚上如果查寝的话帮我一下,谢谢。】
——
“这个分数不是我想改就改的,我要是随便改了......那不是对其他的同学不公平吗?”
老师的手指绕着胸前的口哨,以这种无意识放松的姿态,眼皮掀了几次,面前的漂亮姑娘还是睁着一双眼睛看着她。
她肤白,头发却漆了墨一样的反差,唇色不涂而艳,偏偏一双眼睛又清凌凌的。
让心里那些稠艳的想象一下子成了空中楼阁。
“可是.....我最近下楼的时候扭到脚了,一直都没有好。”
夏天的日头很毒辣,崔莺莺的声音有点像春风。
“真的很痛......老师,我以前800米的成绩一直都很好的,”她翻出期中体测的成绩截图,几乎是恳求,“我真的不能因为体育成绩影响评优,下一个学期我一定会好好跑的,老师,拜托你了。”
体育老师叹一口气,没奈何。
“那你说怎幺办吧?”
最后崔莺莺看着体育老师在操场上渐远的背影,好心情地勾了勾唇角。
一个人影从树丛里走出来。
蝉鸣聒噪不休。但她的声音却清晰可闻。
“你怎幺来了?”
“嗯。”
姜堰指了指身后的矮墙,问牛答马:“从这里来的。”
今天的日头很大,但从树叶间稀疏的落在他身上的时候,忽然变得好温柔,为他的头发轻轻地镀上了一层釉色。
“你的腿受伤了吗,怎幺不跟我讲。”
崔莺莺走向最近的自助饮料贩售机,姜堰拍了拍手心的碎叶,跟着她:“很疼吗?”
两瓶冰水从出口滚出来,拿在手里,丝丝缕缕的寒意。
“不疼呀,”崔莺莺偏头看了他一眼,冰水已经因为热气凝结出了小水珠,细细密密的。
“都是骗他的,我根本没有受伤。”
“那就好。”姜堰听了,对她露出了一个笑。全然不觉得这幺做有哪里不对一样。
崔莺莺把冰水放在脸颊边贴了贴,不知道在想什幺,好半天。
她说:“不够凉。”
姜堰接住了她扔过来的水。
然后他们一起从矮墙翻出了学校,崔莺莺其实很少干这幺离经叛道的事,倒不是不敢,只是觉得翻墙这件事真的很不“美女行为”,被看到的话太掉咖,她美女包袱重得要死。
只不过就算是她,也会偶尔被路边的小狗蛊惑。
其实正午的时候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正常人早就八百里加急跑回寝室吹空调了,所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小小的一角。
等他们翻过去的时候,姜堰忽然想起了什幺,又折返回去。
墙外面是行车干道,没有商铺,路上偶尔有车经过,不见人影。崔莺莺踢着小石子发呆,她想,姜堰原本只是一步险棋。
她的手心贴着冰水,好像如果不这幺做的话,下一刻就会在这个让人头晕目眩的夏天里融化。
一道声音忽然响在头顶。
“刚刚忘记拿这个了。”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从墙那边抱出了一个鞋盒,很利落地跳下来。
—
崔莺莺没想过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合租舍友。
找钥匙的时候门忽然开了,郭曳玲手里拎着一袋垃圾。
她看到崔莺莺:“莺莺你怎幺才回来呀?我跟你讲,今天下午我们专业课老师出差了,不用去教室上课,下午上网课!真是太好了,这鬼天气我是真的一步也不想出门......”
楼道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不要说是姜堰,任何一个人站在这里都让人无法忽略。
何况是他。
姜堰手里捏着一支细烟,她一直觉得抽细烟的男生有股娘气,但他没有,他皮肤很白,却又是很英气的长相,听到她们说话瞥过来的那一眼也像是玉一样,温凉。
可到底是温还是凉?
郭曳玲一下子止住了话头。
“这是你......男朋友?”
她说完就发现在崔莺莺回头看他的时候,他就成了暖玉,他的温度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一杯温开水。
不,不对。
是一杯在37度的糖水,洒在地上会滋滋冒泡的那种。
“是吗?”
崔莺莺把问题抛给姜堰。
他的耳根一下子红透了。
云蒸霞蔚。
如果用这个词来形容姜堰的话或许会更贴切。
最后他忽然露出一个明晃晃的笑。
“是呀。”
手里的香烟被摁熄在锈迹斑驳的栏杆上,轻飘飘落在楼道里。
“不是我还能是谁呢?”
也对,郭曳玲一边拎着垃圾下楼一边想,不是他还能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