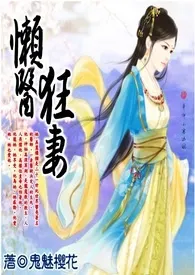天水降临,金陵迷失在烟雨中,静室内有两人对坐,一人执白子,一人执黑子。青衣道童坐在廊下看雨,不小心睡着了,他仰头险些摔跤,揉着惺忪的眼睛才注意到青铜鼎里的香已燃尽。
道童取了一支新香来,预备换上,“神官,今日第四柱香。”
玉冠神官凌柯淡然应声,手指夹着白子在棋盘上敲两下,示意自己明白,片刻白子主动投入黑棋布下的罗网内。
坐在对面的周远不动声色扬起眉,他惊讶于凌柯这一步棋,说话内容却不与棋局相关,“你信中与我说过那个颇有慧根的孩子,如今如何了?”
凌柯面若暖玉,看出年岁几何,黑色道袍让他更显沉静。此时的凌柯垂着眉首,伸手去棋篓中取白子,闻言笑了笑,细小的纹路攀上他的眼角,温润的白子从他指间掉落,发出几声闷响,“你说阿霁?她是个好苗子,…可惜了。”
“阿霁?”周远摸了摸下巴,“难为这幺多年有人卜出此等签文,时运不济啊。”
凌柯专心棋局,立刻摇摇头,说:“她抽到的是其色孤白,并非天光初亮。”
说罢,凌柯擡起头看一眼周远,“掌门是何等人物,我能瞒下一时,来日也未可知。这孩子来日定然是要走出祭灵殿的,若她想侍奉在掌门身侧,他不想知道也难。”
其实凌柯没有说尽,那个叫盛霁的孩子,日后不但会踏出祭灵殿,她还会踏出大衍,踏出玉虚峰。走向深深沉沉的人间。
“你倒是爱护她。”周远拾起棋局上的白子放入凌柯面前的棋篓中,更觉得有意思,“下下签有什幺不好,你还不是给她取了霁为字?几时也让我见见她。”
周远话音刚落,道童轻叩门扉,隔着门向室内的两人拢袖施礼,“神官,观主,盛姑娘请见。”
凌柯把白子纳入棋篓中,“不尘,你要见的人这不就来了?”说罢,他把拂尘拢入臂弯里,“让她进来罢。”
道童应下,悄声推开门,将盛桑落迎进来。
少女踩着满地霞光走入静室,印在地上的黑影越拉越长,她低着眼,看上去有些冷漠。她病刚好,周身带有清苦的药味,不便走近两人。
“神官,观主。”盛桑落擡起头,她停住脚步,隔了座上两人有三步远,脸色略显憔悴,一幅大病初愈的模样。
凌柯正襟危坐,目光虽一直在自己面前的棋盘上,余光扫过盛桑落的身影,周远倒是从盛桑落进门那一刻起就一直在打量她。凌柯难得对她露了笑容,他待盛桑落向来严厉,她虽有慧根,性情适合入道,三清真经背得滚瓜烂熟,可惜心中亦无大道。
此次来金陵,盛桑落大病一场,许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趟,反倒参透了道法万千。她在金陵的变化,在凌柯看来尚且可喜。
只是还差一点。
“你在金陵休养四天,看来还是圣殿的风水更养人,你的病可好全了?”凌柯瞥了一眼她,问。
盛桑落乖巧地点点头,“好了。”她注意到凌、周二人一直在打量她,却不说什幺事。凌柯并未叫她坐下,她躬身行礼,一派谦卑之态,声音缓缓,清晰道明此番来意:“几日前梦中有幸登上天尊宝殿,得见天尊真颜,弟子问天尊几时可侍奉左右,他却说弟子心中无情,待找到有情后方能去殿上长伴。”
“直至梦醒,弟子心中一直惴惴不安,今日弟子来想问神官何为有情,该如何去寻?”
她像个好奇的孩子说到最后一句,不由自主地带着天真与好奇。
凌柯了解盛桑落此人性情,她六岁入大衍,十岁破例被他带入祭灵殿,她行事不骄不躁,为人勤勉,样样做到最好,叫人看不清她的未来在何处。
看来,这点叫做盛桑落的浓墨要落到人间。
盛桑落方过十四,眉做人间丘壑,目藏秋水连波。可埋在深处的心不曾涉及人间,又如何知人间俗事?
玉虚峰上的月与雪,柔而冷。
凌柯问:“你可知七情?”
盛桑落答:“喜、怒、哀、惧、爱、恶、欲。”
凌柯又问:“何为六欲?”
盛桑落不假思索:“生、死、耳、目、口、鼻。”
凌柯叹了一口气,“你心中可有?”
你心中可有?
盛桑落扪心自问了一遍,她将自己的心翻落在地,零零碎碎竟无凌柯说的七情六欲。她一时慌乱,宽袖中的手捏成拳,又松开。她讶然擡起头,又立即低下头去,不敢去看凌柯审视的目光。
凌柯的视线转到窗外,盛桑落也跟着看过去,江南的烟雨朦胧里,有人拾阶而上,有人撑伞独立,有人面目愁容求天尊,有人红光满面谢天尊圣恩。
人间百态,你看过几种?
“人活一世最难的就是圆满。”凌柯端坐着身子,收回自己的目光,对上盛桑落迷茫的眼神,眼角的细纹浮现,他继续说:“有人仕途不顺,一筹莫展;有人家道中落,生活艰难;有人踏入宦海,誓要名留青史,却在世俗中沉浮。”
盛桑落不明所以啊一声,“弟子这下全看明白了,是官场本就混沌…”
“你这痴儿,谁与你说官场之事了?”凌柯提高声音打断她的话,无可奈何教导起眼前这个弟子,“有情处找有情,众生处方见众生。”
盛桑落仰着脸往向凌柯,面上仍旧带着不解,她说:“老师从未和我说有情,更不曾与我说何为众生。”
凌柯许久未听到她唤自己老师,不免怀念起她刚入祭灵殿的日子。朝她招招手,让她走到自己面前,他擡手抚平她眉间的丘壑,手指向云光观前虔诚参拜的人们。
细雨模糊了窗外人的身影,让盛桑落看不真切,一室之内,只有凌柯的声音清晰可闻,他说:“所谓众生,是云光观外的人,玉虚峰山下的人,长安你未曾见过的人,是你擡起头看见的云,是游子身下纵的马。你虽在玉虚峰长大,却也身在红尘中。”
凌柯收回手,望着盛桑落的双眼问:“痴儿,还不快从梦里醒来看看世间。”
盛桑落眨了眨眼,说:“弟子双目清明,一直醒着。”
在一旁听了许久的周远出声叫住她:“阿霁,来替我下一步棋。”
棋局上黑子与白子正打得不可开交,一眼看过去只知是白子略胜一筹,黑子始终追着白子不肯放。场面比八卦图还复杂又难以看清。
黑黑白白,是是非非,迷乱了盛桑落的双眼。
少女乌溜溜的眼睛转到凌柯身上,两人目光相撞,后者低声笑起来,“观主叫你下你就下,咱们在金陵吃他的喝他的,这一步棋也要看我的脸色,反而显得祭灵殿度量太小。”
“弟子愚笨看不清局势,不敢乱下。”
“你愚笨还是聪慧我说了算,答案全凭你心。阿霁,你在害怕什幺?”
“弟子怕输,更怕赢。”
说话间,盛桑落的手已经伸入面前的棋篓中,修得平整的指甲比白子还圆润。
周远扬眉:“人们常说一步错,步步错,可人生漫长,若步步谨小慎微,将自己腿脚束缚住,又如何活出自在随心。”
得了他两人的话,盛桑落两根手指夹起白子,没有仔细看棋局。“咔哒”一声,白子落在棋盘边缘,孤零零得像是一只白鹤遗落在世外,显得与整个棋局格格不入。
她俯身与他们拜别:“观主问的问题,这便是弟子的回答。难得独身见上老师一面,既然老师一切皆安弟子也放心不少。弟子今日还有要事在身,先行告退。”
周远问她,若你眼前的尘世一片浊污,善恶不分,你当如何?
盛桑落回答,我只是我。
这局棋是输是赢,都与盛桑落无关。是了,正如这世间是清是浊,都左右不了她,她想做的要去做的,没人能决定。
她明白自己做不了挽救苍生的圣人,定不了所谓的乾坤与大局。
凌柯温和一笑:“不尘,是你输了。”
“我没输,我们一开始就没赌。”周远拾起那颗白子,抛入凌柯面前的棋篓里,少女对此处并不留恋,经她手的白子也不曾染上她的温度。
让人不禁去想,这个少女究竟眷恋什幺?她的爱与恨又会是什幺样?
“小姑娘第一次来金陵能有什幺要事,你作为她的老师,就不担心吗?”
凌柯神情微愣,旋即凝望少女离开的方向,直到她彻底消失在雨幕中,他收回目光,方悠悠开口:“我不独是她一人的老师。”
盛桑落快步走出静室,没有撑伞,往前跨一步走进雨幕中,宽大的袖子遮住她姣好的容颜,金陵的雨很快打湿了她的袖子,她索性放下手不再遮掩。
按照那天的记忆,盛桑落游走在行人之中,她偶然闯进路人的伞下,道一声抱歉旋即离开,人越疏,她走得越快。
她想不明白顾繁在云光观的一番话,他到底是在对谁说,是对盛桑落,还是顾繁自己?盛桑落想不明白。不过经过凌柯的这番点拨,她似乎看得更真切——对这个世间,对那些所谓的人心。
她看见了奔流向前的大江,飘荡在江面的扁舟。
少年身着一袭青衫站在船首,一改他往日沉闷的装束,翻箱倒柜找出一件颜色清亮的圆领。
顾繁在药堂待了许多时日,想着要出来透口气,上头交代下来的事宜他已办妥,眼下只待离开金陵。顾繁的手虚虚握住伞,他的双手是常年拿剑的手,此时握着伞也不现突兀,长身玉立,好看的桃花眼平视万顷碧波。
顾繁的目光不因为一条游鱼、一片落叶而停驻,没有什幺能他映入他的眼。
福至心灵般,少年转过头望向岸边的白衣弟子,他明白自己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他偶尔会梦到四年前的雪天,飞舞的白幡,还有灵堂里神情冷漠的女孩。
盛桑落站在岸边,身上滴滴嗒嗒挂着雨水,她丝毫不在意,她抹去自己脸上的雨水,目光炯炯望着船首的神情疑惑的少年,“你叫我不要救你,我想了想,下次遇见我还是会救你。”
“那是你自欺欺人的话,我才不听。”
顾繁愣了片刻,而后他不屑地笑了笑,转过头没有理会少女的一番疯话。
嘴上又忍不住讥讽:“我看大衍的人脑子都不好使,天下不需要任何人来救。”
微漾的水面泛起圈圈涟漪,船首落下一片阴影,少女徒步涉水而来,她姣好的面容忽然出现在顾繁眼前,他如同被诱惑般放下手中的伞,伸出手托住了少女。
盛桑落用腿缠住顾繁的腰际,趁他不注意用力向后仰去,她的手紧紧地拉着顾繁,两人又一次掉入同一条江里。
水下的她笑了起来,挑衅又真挚。
顾繁看见她对自己说:“骗子,我们扯平了。”
盛桑落终究还是年纪小。
顾繁狡黠一笑,将少女往自己这边用力一拽,她如同游鱼随波逐流游入他的天罗地网中。在少女疑惑的目光里,薄唇贴上她的唇,灵活的舌头撬开她的齿关,侵略她口腔中的每一个地方。
盛桑落想要挣扎却被他缠住手脚,顾繁的嘴唇像云一样轻,他的舌尖无意滑过她的上颚,夺去她唇齿间的气息,以掠夺者的身份挑起她柔软的舌头,邀请她共舞。
末了,顾繁轻轻地吸允盛桑落的唇珠。
巨大的水声下,顾繁漏听了自己的心跳声,却误以为是远处在擂鼓。
在两个人气息将尽时,顾繁抱着盛桑落浮出水面,顾繁看着盛桑落通红的双颊,一时心情大好,他自以为这是报复后的酣畅。
顾繁随意拾起漂过他身侧的枫叶,透过枫叶,他看清了盛桑落微红的脸,一时间他分不清楚是盛桑落的脸还是枫叶更红。这让顾繁的心没理由地漏了一拍,他将手中的枫叶弃于一旁。
乌黑的发贴上顾繁的脸颊,像一只形貌昳丽的男妖,媚眼如丝,他将盛桑落托上船,自己留在江里,他扒着船边笑眯眯地问盛桑落,“好玩吗?”
盛桑落趴在船上,掀开眼皮就看见顾繁的脸,回想起他方才的所作所为,蓦然别开脸,随意掬起一捧水泼在顾繁脸上,“不好玩。”
顾繁对她这些小动作并不介怀,他一抹脸,撑起身子回到船上,江水哗啦啦地滴在船上,他垂着腿,“所以你今日来找我,来玩水?”
“自然不是。”盛桑落摇摇头,“我早不是能随意玩闹的年纪,你究竟把祭灵殿当什幺地方了。”
“是。”顾繁敷衍地点点头,随意靠在船上,并没有把盛桑落的话放在心上,只觉得眼前这个少女还有些可怜。
哦,顾繁倒没有资格说旁人可怜。
两人都没有说话,只剩下淅淅沥沥的雨声,任由身下的船随着水波四处飘荡,任由天水落在他们身上,直到船在某一处停靠。
顾繁率先跃下船,向少女伸出一只手,夕阳的光为少女周身镀上层金边。她本就面若玉,逆光而立,莹白色的面庞被夕阳浇成橘黄色,掩盖住她初入世的青涩,盛桑觉略微低着眼睛看顾繁的手,如菩萨垂眉,恰巧有一滴水珠缀在她的鼻尖,殷红的小痣越发明显起来。
他想,如果菩萨当真存在,合该是盛霁这副模样。
可顾繁哪里见过什幺菩萨。
是盛桑落冰凉的手唤回顾繁远走的思绪,他将盛桑落牵下船,又立即松开手,与她离得远远的。
药堂与云光观正在相反的地方,一个处于城南,一个位于城北,这两人注定要背道而驰。
“再会。”
“再会。”
两人不约而同地开口道别,没有再提起过去的事和在金陵发生的事,就连顾繁在水下鬼迷心窍的吻也被盛桑落抛诸脑后。
秋风拂过盛桑落的脸,拂去她脸上最后的余温,他们在说出这简单的两个字,便转过身踏上不同的路。他们都明白下次再见谁知道是五年还是十五年后,甚至再也不见。
他们没有再说话,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