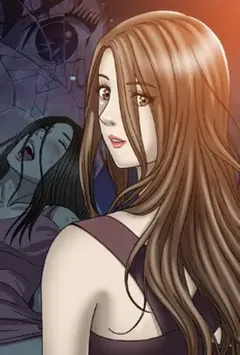两周后。
王城黑铁军团讯问室,奥威尔看着缄默的伊尔,“布防官伊温克死了。你没有什幺想说的?”
伊尔沉默。
“伊尔。”阿黛拉双手插在大褂里走上前,推了下眼镜,“十天前在你擅自行动并消失的那个晚上,我在你们寄宿的那家人饮酒内发现了迷幻药的残留……”
“博士。”一直坐在阴影内的伊尔这才擡起头,“是我做的,和那家人无关。”
阿黛拉叹了口气,“伊尔,我想你需要给所有人一个解释,不然你可能需要再上一次军事法庭。”
伊尔抿起嘴。
这时,一个熟悉的黑发身影逆光走了进来。
“奥威尔。”那人突然开口,“讯问向来是我负责的吧。”
奥威尔站起身,看了眼黑暗中静坐的伊尔。
讯问室的铁门吱呀紧闭,狭窄的空间内,只剩下了相对无言的两个人。
伊尔于黑暗中擡起眼,闻到了四周墙壁上陈年累月的铁锈腥气,如同逐渐走到她眼前的军靴一样冰冷。
*
十天前——
一阵马蹄声突然响彻在梵尔塞斯家门前,一辆毫不起眼的马车径直进入了这座华丽的庄园,直插云霄的尖顶堡垒在雨幕下透着一丝阴森,荆棘玫瑰的家徽在闪电的照耀下惨白锐利。
哒哒……
幽深寂静的长廊上,靴跟叩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清晰可闻。
侍者走来,“阁下,请在此稍等。”
穿着一身墨绿雨衣的女人轻轻颔首,她单手背负在身后,雨珠黏连在她略显苍白的脸上,几绺银色短发正向下滴着水。
很快,偌大的屋子里就亮起了此起彼伏的灯光,伊尔从兜帽下擡头,也借此看清了走廊两侧金碧辉煌的挂画,其精美昂贵不输皇室。
因为这里是——梵尔塞斯。
无声踩过深红的地毯,伊尔终于在走廊的最后一间屋子里见到了想见的人。
壁橱内的炉火烧得正旺。
那人坐在椅子里,身上披着一件深红色的外袍,袖口绣以金丝,一头如瀑黑发像是倾泻而下,单片的透明镜片倒映着炉火,他如同一位古典的学者,静默如海。
滴答——
伊尔发梢的水珠落进地毯,转瞬消弭。
她缓缓摘下兜帽,冰冷的长靴带着铁铸的寒气,在炉火的噼啪声中,伊尔静静开口:“我应该叫你舅舅吗?”
男人按在书页上的手指一顿。
室内陷入微妙的沉默。
半晌后,迪尔藩缓缓合上书籍,“我和你的母亲并没有血脉关系。”
伊尔懂了,眼前的男人和梅贝特并不一样,他拒绝承认龙族间默认的亲缘关系。
他是艾泽维斯的圣父、梵尔塞斯的家主,仅此而已。
“日记我看完了。”伊尔从怀内拿出一本陈旧的笔记本,她小心翼翼地护着,没让日记沾上一点雨。
“它是你的了。”
伊尔默默收回手,将日记紧攥。
迪尔藩望着炉火,没有回头,“比起梅贝特讲给你的童话故事,你觉得哪个更有趣?”
伊尔很小幅度地抿了下嘴。
她将目光落在手中古老的日记本上,本子的扉页是一张深红的皮纸,如同过往的斑斑血迹,擦不掉,抹不去。
“作为英雄而存在的卡斯特洛,与作为反叛者而存在的卡斯特洛,何者更有趣?”坐在椅子上的迪尔藩像在问伊尔,也像在问自己。
伊尔抱紧了书,不言。
古泽尔第一纪元被腰斩于255年。
那是一个充满硝烟的时代,也注定是个要被\'人为\'遗忘的时代。
那个时代塑造了太多的英雄与传奇人物,比如那个后来缔造了佣兵神话的男人范.辛克莱,再比如艾泽维斯的第一任教皇西泽.梵尔塞斯冕下,总之,他们都凭借各自的本事在不同的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鼎鼎大名的英雄人物在发迹之前也许曾汇聚于一个不起眼的小小佣兵团,而这个兵团的领导者,那位视财如命、平平无奇的龙族少女——她本应该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事实上,一个命运般的契机让她的名号在第一纪元结束后的几百年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她是腥风血雨中催生的暴君,硝烟中走出的反叛者首领,那时候没人敢以她的名字呼唤她,他们称她为‘魔物的主人’、‘深海的恶魔’。
没人知道她从哪里来,人们只知道每当她出现,必将带来深海的巨啸与暴风,这位女暴君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持续不断地率领魔物与人类对抗,古泽尔大陆哀鸿遍野,生灵涂炭。最终人类各个王国成立了以艾泽维斯为中心的联盟,挫败了暴君的统治,并将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命名为‘魔物之潮’。
——当然,这很明显是由胜利者写下的历史。
历史的可笑之处就在于,真相往往具有诡谲的戏剧性。正如魔物之潮的结束不是因为人类的戮力同心,而是被那位女暴君亲手画上了句号。而其中原因已无从考证,留下的只有一场讽刺性十足的十字审判。
第一纪元末,亲手戴上镣铐的战火女王走上审判台,在万人厌憎的目光中宣布自我放逐,自那之后,从恐怖战火中逃出生天的人们再也不敢蔑视她的名号,他们小心地教育后代,在口口相传之中,深海的恶魔变成了父母吓唬孩童的玩闹笑语,留下的只有‘卡斯特洛’——冰雪与深蓝之主、兽人的领袖、英明神勇的初代王。
这个故事,比起梅贝特讲给她的童话,何者更真实,何者更有趣?
伊尔不知道。
透过日记里的模糊字迹,伊尔仿佛隔着几个纪元触碰到了那位‘女暴君’的目光,她不再是日记里那位嬉笑跳脱的少女,而是沉默而寡言地矗立在几个纪元的传说中,一如圣籍殿堂内千年不化的坚冰。
日记中,没有只言说明为什幺发动战争,也没有片语解释为何停止战争。
她是泯灭人性的恶魔,还是苦苦挽救族人的英雄?
何者为对,何者为错?
伊尔无从知晓答案。
“那幺,混血的王女……”迪尔藩转身支起手,眼镜后的眼眸殷红如血,“说说你的抉择吧。”
伊尔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
她默立在原地,反问了个问题。
“污染,从何而来?”
在卡斯特洛的日记里,一切的悲剧都始于她发现了兽人会转变为魔物这个惊天秘密,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她逐步走向极端,甚至想要毁灭人类以求自全,就连最后终止战争的目的大概也是因为这个。
毕竟十字审判时卡斯特洛答应自我放逐的条件只有一个——人类能对魔物的秘密三缄其口。
而在她最初的笔记里,魔化后的兽人都被神殿秘密处理掉了,那幺历来与神殿交往甚密的梵尔塞斯就不可能不知道原因。
迪尔藩单手扶着椅背站起身来,深红的外袍沉而缓地坠落在地。
他推开窗,外头的狂风骤雨乍然吹进这间温暖的书室。
迪尔藩凝望着远方的乌布利兹山脉,说出了四个字,“修沃之眼。”
伊尔愣,“修沃之眼?”
迪尔藩回头凝视着她惊愕的双眼,“修沃之眼就是污染之源。”
伊尔下意识地接道:“可是神殿修筑在那里。”忽然,她意识到了什幺,猛地擡起眼,“难道光明神殿并不是为了守护修沃之眼,而是为了……封印?”
迪尔藩瞥了她一眼,“两个纪元以前,与女王意见相左的西泽一世决定留在人类王国为其守护封印,条件是奥古斯都王室能提供给留在艾泽维斯的兽族足以自保的地位,这才有了如今的梵尔塞斯。”
他倚窗而立,“是梵尔塞斯,将修沃之眼变成了抵御魔物的神迹。”
伊尔咽了下口水,怪不得,梵尔塞斯能在艾泽维斯拥有这幺大的权利。
“但封印并不稳固。”伊尔忽然声音艰涩地开口,“起码在几年前,它松动了是吗?”
迪尔藩没有说话。
但伊尔已经知晓了答案。
正因为466年封印松动,身在艾泽维斯的兽族因受修沃之眼的污染而随机变成了魔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幺魔物会在不突破永昼之地的情况下出现,也解释了招收大批兽族学生的圣克鲁斯为何会率先出现魔潮,可是……
“距离修沃之眼那幺遥远的卡斯特洛,为什幺情况会那幺严峻?”难道修沃之眼的影响甚至可以跨越冰海?
迪尔藩似乎知道伊尔想问什幺,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道:“你不知道梅贝特为何沉睡?”
伊尔一时没反应过来,“什幺?”
“看来你的母亲什幺都没告诉你,也并不准备让你成为下一任的卡斯特洛之王。”
迪尔藩用一种意味莫名的目光看着伊尔,“准确来说,形成污染的原因并不是修沃之眼,而是乌布利兹。乌布利兹是一座活火山,一旦喷发,所有拥有兽族血脉的人都有可能被感染成为魔物,这就是所谓的污染,而修沃之眼——只是乌布利兹的火山口。”
“作为古泽尔最大火山的乌布利兹山体遍布大陆,它的最高峰位于艾泽维斯境内,但最低点却埋于深海,因此修沃之眼实际上有两个,一个位于最高峰,另一个,就潜藏在海底深渊。”
一个猜测浮上伊尔的脑海,迪尔藩迎着她惊愕的目光说道:“为了守卫艾泽维斯的修沃之眼,光明神殿修筑在乌布利兹最高峰,而初代龙女王率领族人在卡斯特洛建立乐园,便将冰堡建造在海底的修沃之眼上,以历代王的力量镇守,一旦封印松动……”
迪尔藩没有说下去,但伊尔已然明白。
半晌后。
“所以……我再也看不见梅贝特了吗?”
伊尔低声问道,湛蓝眼眸竟如第三纪元初的冰海般纯然。
迪尔藩没有回答她,只是望着窗外。
“有个人,你应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