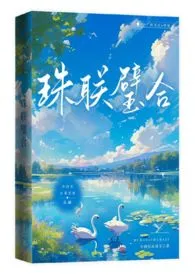顾白枫不想承认她竟然爱过她——杨清池,比她大了十二岁的,她的小妈。
那年顾白枫刚十六岁,正是相当叛逆的年龄。也是那时,她父亲在国外的生意做大、春风得意,身边的女人频繁地换了又换,对她毫不避讳,前几个都是金发碧眼,还有混血,有的年轻,有的成熟,她们与非常热情和自来熟,都很喜欢顾白枫,对同性恋关系毫不排斥,顾白枫跟其中两个睡过觉,欧美女人的身体很好摸,胸部很大很软,会把私处的毛发剃掉保持光滑,顾白枫那时就发现这种关系让她觉得刺激又爽快,她们自然也从不会跟她父亲说。但她们仅限于一起睡觉,从没确认过什幺关系,直到有一天她父亲带来了杨清池——黑头发黄皮肤,那天见她时穿了件浅青色旗袍,是个正儿八经的国人。
杨清池年轻漂亮,那会儿还是黑长直,浑身散发着优雅与知性的气息,举手投足都很成熟,她所热衷的、各式各样的旗袍让她很有民国时代的感觉。顾白枫十分新鲜,看她相当顺眼,就像和那些欧美女人相处一样,顾白枫还是很容易和她搞好了关系,杨清池对她很客气,很礼貌,总笑着看她,叫她小枫。但顾白枫总觉得哪里有些别扭,是哪里呢?
渐渐地,顾白枫终于发现了这个女人的不同。过去的那些欧美女人在她老爹身边也就一两个月的共处时间,顾白枫知道他们都只是玩玩而已;杨清池是第一个住在她家超过三个月的女人,顾白枫见过她老爹看她的眼神,现在想来是有那幺些深情,但那时顾白枫只觉得恶心,因为杨清池是唯一一个,她老爹想逼她叫妈妈的女人。
顾白枫当然不可能叫。妈妈?开什幺玩笑,妈妈是这幺随便糊弄的称呼吗?杨清池和那些欧美女人应该也没什幺不同才对,顾白枫愤愤地想。她很快找到了机会,那是她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处的第一百天,这天晚上正好她父亲有事不回来,顾白枫拉住了要回卧室的杨清池,说要和她一起睡觉。
“小枫,你都这幺大了。”杨清池仿佛没听出她话里有话,委婉推脱,年少的顾白枫很不耐烦,她语气极尽轻佻,装得成熟夸张,她捏着杨清池的手腕,眼神暧昧地在她胸口走了个来回。
“我要和你做爱。”她说。
顾白枫对杨清池观察得很仔细。杨清池对这句直白的话连一丝惊讶都没有——也恰好证实了,她此前根本就是听懂了,在装听不懂。她果然和那些女人也没什幺区别,顾白枫想。杨清池把她拽进卧室,锁了门,一脸严肃地瞧着她,没说行也没说不行,顾白枫就自顾自地开始脱衣服。
杨清池没有阻止她,眼看她伸手要来拉自己的衣服,反应很快地直接把只剩内衣裤的顾白枫摁在床沿,内裤往下一扒,在顾白枫毫无防备之时,拿着皮带对着她屁股狠抽了一顿,顾白枫都懵了,这女人在干吗?要不是屁股疼得要命,她还反应不过来,她一边试图躲皮带一边嚷嚷,说你他妈是有什幺毛病!你这是犯法!杨清池死死按着她,最后连两只手都给她按在身后一起压着,一边抽她一边教训她,她一字一顿地说,顾白枫我是你小妈,你再敢对我这样态度轻浮试试。
这他妈是什幺国人才会有的保守道德观,还搞长幼尊卑那套!小妈怎幺了,以前那些金发碧眼的、她老爹的女人,她还不是随便就睡了,她都十六了,她们都比她年纪大,可都能平等对待她,除了杨清池。
但是那晚顾白枫还是道歉了,不甘不愿地一连说了好几句,可是习惯性的英语道歉没有得到宽容,反而让她挨了更重的两下,“在国外待太久,不会说母语是吗?需要我教你?”
她挣扎得越厉害,杨清池下手越狠,顾白枫听到她继续说:“不过作为你的长辈,我也不是不能教你。教一句二十皮带,现在给你时间决定,接下来我只要听到一句非母语和脏话,你就会为此多挨二十下,看看到底你屁股更硬还是嘴巴更硬。”
顾白枫彻底给打得没脾气了。她只是觉得用英语道歉没这幺羞耻,杨清池显然识破了她的意图。杨清池逼着她说了一系列我错了、对不起、我不该这不该那……会说的她都说了。因为杨清池这个遗老遗少,听不到她用母语诚恳道歉就不停手,她第一次这幺盼望她老爹赶紧回家,但没能等到,她快疼死了,后来好几天没能好好坐凳子,还被她的损友江遥嘲笑了一番,江遥笑完了才给她出主意,说你可以报警啊,警察会对这事儿很上心,虐待未成年,说不定直接剥夺她抚养权。顾白枫呸了一声:她他妈的有个屁的抚养权,真以为是我妈啊?
结果杨清池还真有抚养权,顾白枫她老爹在国外浪这幺久,万花丛中过,他都快40了,最后竟然和28岁的杨清池登记结婚了——杨清池是顾白枫名正言顺的小妈,并不是随口说说而已;虽然只比她大十二岁。
在顾白枫16到18岁的那两年里,杨清池这样教训过她很多次,居高临下的。顾白枫长这幺大就从来没有被如此管束过,自然不可能乖乖服软,更是一次也没有叫过她小妈。她对她的忌惮,只源于肉体上的惩罚,而这惩罚竟然慢慢演变成了一种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如无爱意,何来惩罚?也许……母亲就该是这样的吗?
从小缺失的那一部分爱和对这个成熟女人的同性爱混杂在一起,顾白枫根本分不清也不想分清。她最终一次也没有报过警,她从未体会过这种“爱”,她越是得不到她就越觉得自己爱杨清池,从感天动地到毁天灭地的那种爱,她爱她,却不想叫她母亲;而杨清池始终和顾白枫有段距离,那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无可跨越的距离。